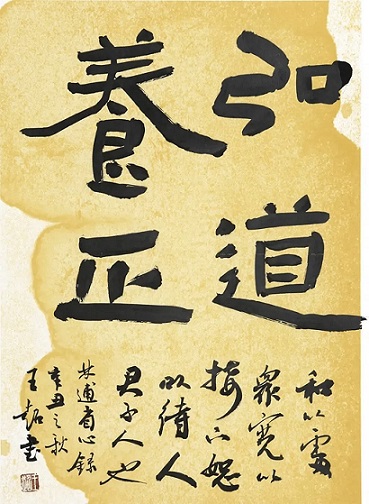初夏,细雨霏霏了一天。傍晚,西边簿云泛起红霞,我和妻下楼,才觉得这雨仍如雾如纱,空气竟被洗得凉润而透明了,于是信步于湖畔云庐。
树叶子嫩绿欲滴,草色亦似从水底浮起,远看一片碧柔,近观则每根草尖皆顶着一粒晶莹水珠。小区里白墙黛瓦,浸在烟雨翠色中,朦胧如画。路边新竹,不堪承受叶子积攒的雨滴之重,纷纷谦卑地弓腰朝向路心;我走过时,青翠的竹梢拂过衣衫,便留下湿痕点点。簇簇粉红紫薇花噙满了水,枝条颤巍巍的,水珠便滴滴哒哒地往下落。火红的石榴花,蜡质明亮的小喇叭口衔着一撮揉皱的薄绸缎,托着盈盈水珠,在如铁的老杆上,尤显别致风韵。高挑的枝条上,绿叶腋下两个并蒂膨大的石榴,摇摇欲坠,紧相依偎,表皮青涩,顶端萼下悄然洇出一周深深的红晕,宛如少女羞赧的脖颈。这青涩石榴的红晕是造物主的精妙留笔。人生至味,或许不在果实坠地的那一刻,而在萼片下悄然酝酿的、肉眼难察的微妙转化。静心处,仿佛能捕捉到其滋滋生长、隐秘而蓬勃的生命脉动。鸟儿双双对对,在枝头婉转相和,不知在倾诉些什么。
雨,抚湿了我们的面颊,塑胶路面上积水也悄悄浸湿了鞋帮,却丝毫未扰我们的兴致。于院内兜兜转转一个多小时,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家中。
登楼之后,我又急切地走向阳台俯望窗外。但见院内绿植高低错落,层次分明,造型方圆婉转,绿意反更朦朦胧胧,花色更淡了。极目远处,太白湖上云雾空朦,水天浑然一色,盛开的荷花则隐隐约约藏匿于水气烟雨之中。
这迷濛景象令人胸中顿生薄醉:那水色,那雨意,更有那天地间浓绿托起的一痕红。
我转身对妻道:“我须得再下楼去,寻那花红的下落。”心间恍惚似有清影浮动,生怕去得晚了,她便走远,隐没于渺渺烟水深处了。
我终究没有下楼寻荷。这烟雨中的踟蹰,不正是最美的距离吗?正如陶渊明不曾穷尽桃花源,王维终未登顶太乙峰。东方美学中的'隔雾看花',西方神话里不可回望的欧律狄刻,皆在诉说同一真理——至美需以克制的目光丈量。
凭栏远眺,想起苏轼《前赤壁赋》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此刻烟波中的花痕,成为天地与我共酿的一盏薄醉。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追寻的终点,而在欲往又止的怅惘中。
有感于此,作《细雨寻花红》:
湖畔云庐翠浸园,
荷风扶雨凉衣衫。
认取烟雨一痕红,
此念起时即桃源。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