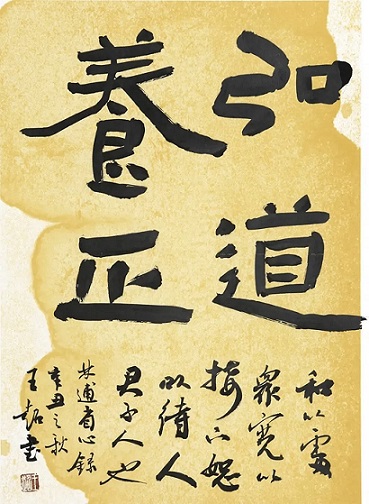腊月的风裹挟着霜花掠过屋檐时,老家锅屋的窗棂便开始溢出白汽。
母亲把柴火备足,灶台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口铁锅刷得锃亮,加了半锅水,在风箱的“呼哒”声中,旺盛的火苗正舔舐着锅底。父亲蹲在院角燎猪头,火烫的三角头烙铁舔过黑黢黢的皮毛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响,焦香混着松脂味在整个院子里游荡。屋檐下的麻雀左顾右盼,叽叽喳喳“瞅议”着院中忙碌的家人。
母亲在面盆里把面团来回倒腾揉压,扬起的面醭像白蝶掠过春溪。案板上的面团渐渐膨胀成圆月,她把揉好的面掐分成若干剂子,大姐二姐则在旁边给母亲打着下手。蒸笼在锅台上摞成宝塔,笼屉最底层是白生生的馒头,往上依次是咧嘴笑的枣馍馍、盘成龙形的花卷,最顶层的“枣山”最为精妙,红枣嵌成层次分明的莲花座,面塑的鲤鱼似要跃出浪花,仿佛随时要游进除夕的时光里。
我蹲在灶膛前拉风箱并不断续添柴火。炙热的火光把脸烤得通红,脊背徐徐渗出汗来。蒸好面食掀开笼盖水汽升腾时,白气裹着麦香枣香扑鼻而来,整个锅屋瞬间变成了云雾缭绕的仙境。浓稠的雾汽里母亲忙碌地用手蘸着凉水从笼屉往煎饼筐里捡拾面食。她鬓角发梢沾挂的水珠透映着柔光,额头不断有汗珠渗出。蒸熟的面食在筐里渐渐冷却,白嫩细腻的表皮像是刚出浴孩童的皮肤甚是令人欢喜。
父亲煮猪头的锅咕嘟咕嘟冒着气泡,油泡在汤面欢快地跳着圆舞曲。父亲说“猪头肉要煮三滚”。第一滚去腥,第二滚入味,第三滚出魂。当那颗煮透的猪头被捞进搪瓷盆时,左邻右舍此起彼伏的“砰砰乓乓”剁馅声便响成了交响乐。急性子四婶家的剁肉声最是响亮;打铁的二坡哥剁馅声最急;会拉二胡的泉叔剁馅声最有节奏。家家争先恐后,仿佛谁家先剁完饺子馅,谁就能先迎来新年。
腊八这天不光熬腊八粥,还要全屋大扫除。父亲用麻绳把鸡毛掸子绑在竹竿顶端,我举着这支“降尘杵”,在房梁间挥舞出千军万马的架势。待灰尘簌簌落下时,阳光正穿过新糊的窗纸,在地面织出菱形的光斑。
镪旧对联是项技巧加力气活。热水浇在门框上,蒸汽里洇湿着褪色的对联。铁铲与木门摩擦的沙沙声里,碎纸屑纷纷落下,“除旧迎新”正应景当下的情形。家庭宽裕的还会给门扇门框重新刷遍黑油漆,门框外沿边槽再填描一条红漆线用来装饰点缀,大门两边悬挂上两个彩纸糊的灯笼,迎新年的氛围便愈发浓厚了。
腊月十六这天,鹅毛大雪下得正紧。父亲牵出自行车要去姥娘家看亲。母亲把两个箢子分挂在车把两边。箢子里装着馒头、纸封的油炸果子、瓶装罐头、一条五花肉和酒。车轱辘碾轧着积雪,发出"吱呀吱呀"的吟唱。
年前要把该看的亲戚都要走到。有时我会跟随父亲串亲戚。长辈们寒暄过后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毛或两毛压岁钱。用红纸包着像片小火焰。到了饭时,亲戚的八仙桌上已摆上菜肴:粉条炒鸡蛋泛着金黄,捏皮的白花生仁配搭着嫩绿的芫荽,白菜粉条炖肉飘着诱人的香。最馋人的是那碗红烧肉——油亮亮的肉块堆成小山,咬一口肥而不腻,软糯可口,齿颊留香,令人回味悠长。
返家的路上看着来来往往走亲戚的行人,自行车、地排车上装着的礼品,道上弯弯曲曲拉长的车辙,心里在想:“脚步为亲”这句话真实在。亲戚间经常走动,感情自然加深。过年不光是吃好穿暖,还有浓醇的亲情和惦记。温暖和爱意流淌,亲情与友情深藏。这份爱在人们行色匆匆的脚步中蔓延,这是独属于我们民间淳朴的交往及礼尚往来。
腊月二十二,院子的一角便支起了熬糖的铁锅。熊熊火苗舔着锅底,把红砂糖熬成琥珀色的糖浆。糖浆拉出的金丝能缠住整个冬天的阳光。做花生蘸、芝麻片很考验手艺。母亲把滚烫的糖浆倒在抹了香油的木框盒里,那里面均匀地铺满了提前炒好的花生仁和芝麻,糖浆遇冷收缩发出“噼噼啪啪”的脆响。她抄起锅铲快速糅合,用擀面杖擀压把花生与芝麻揉成一体,糖饼越压越薄,趁着余温用刀切成一条条短块,最后收纳在囤子里。我站在旁边看得出神,冷不防被母亲往嘴里塞了块糖渣,在嘴里化开时泛起甜丝丝的津液,那香甜的味道至今还能撩拨着我的味蕾。
腊月二十三祭灶。母亲把花生麻糖摆在灶台前的供桌上,说是给灶王爷的“甜嘴钱”。慈祥的灶王爷画像两边红底黄字写着“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的祈福语联队,人们的美好祈愿与祝福都凝聚在过年的这段日子里。
祭过灶后,母亲翻出压在箱底的布票,领着我们去供销社扯新布。藏青色卡其布最受人们的钟爱。售货员用木尺丈量后用剪刀剪开一个缺口,两手用力一扯,“刺啦”一声,惊得不明就里的人赶紧用手去踅摸自己的后腚。不怕大家笑话,在手工缝制衣服的年代,服装开线这种事情太稀松平常了。
母亲给我们兄弟姊妹几个缝制新衣是要熬上几个通宵的。尽管她手指戴着顶针,因煤油灯光线暗不得眼,缝衣针把手攮出血是常有的事。每次母亲都是放在嘴边吸一吸,接着又赶紧缝制。母亲缝制的针脚密得像蚂蚁排队,规规矩矩,整齐划一。缝制好的新衣板正熨帖,穿在身上特别舒适得劲。
腊月廿六,父亲带着我们去赶年集。年集上涌动着春的讯息,整个集市像流动的《清明上河图》。卖插花的摊子最热闹。用彩色蜡纸做的各式各样的花摊前总挤满爱美的小闺女;爆竹摊前则围满半大小子。用板凳支起的苇箔上摆满了红纸包裹的鞭炮和二踢脚,卖炮的把红纸拆开,在一片开阔地上单放“二踢脚”吸引人前来购买。最贵的一挂“雷子”要一块二一盒,父亲咬咬牙买了一挂,剩下的又买了几挂小鞭。我怀抱着鞭炮往家走,纸包在怀里焐得热乎乎的像揣团小太阳,心里自然是美滋滋乐悠悠的。
年三十天刚擦黑,母亲和姐姐们在一旁和面包饺子,我们则围坐在火炉边吃着炒花生听父亲讲故事:“年这个怪物最怕红色和火光,所以人们贴红春联、放拦门棍、燃放爆竹用来驱赶它……”添加的煤块在炉腔里噼啪炸开,炉火烧红了半截铁烟筒,火光映着墙上新贴的年画,在跃动的光影里愈发温暖人心。
我们将父亲发的压岁钱装进贴身的衣兜里,那张小小的纸币像枚护身符支撑起我们内心无限的底气。我摸着兜里的钱,听着远处零星的爆竹声,除夕夜家人围坐,一起“守岁纳福”。有时幸福就是这样纯粹:在寒夜里拥握着温暖,静候着一个新的黎明;在温馨中感受着亲情,共同迎接新一岁的到来。
子时交岁前,父亲郑重地把鞭炮捋好摆放在院中央,等待母亲在堂屋八仙桌上摆置供品。桌面上铺满大红纸,中间放三碗馒头,碗沿贴着红纸剪的窗花。馒头前摆放着苹果、柿饼、桃酥、羊角蜜和糖块等,最后面摆放的是面塑的“枣山”,红枣堆成云朵,面鱼游在浪花里。摆好供品燃起香烛跪拜磕头后,父亲低声念叨着“敬天地神明”点燃引信的瞬间,火鞭瞬疾炸响。 整个村庄顿时陷入鞭炮的海洋里。东家放罢西家放,前院炮声未息,后宅接着响起……村子在炮声中震颤,火光红透了半边天。这是我们男孩子最刺激和最忙碌的时刻。跑张家窜李家去“抢”拾未炸的哑炮仗。把哑炮一掰两截,露出黑亮的火药。将燃着的荆香凑近时,哑炮呲出的金花映着小伙伴们张大的嘴巴,内心满足极了。心目中,那种感觉比后来所有见过的烟花都绚烂、更有趣。
大年初一天刚微亮,我赶快在棉袄棉裤外面套上新衣去外面遛达逛逛。尽管天气寒冷,但在新衣服的加持下竟一点也不觉得了。走在雪地里,新棉鞋踩出“咯吱咯吱”的节奏,仿佛整个春天都在我的脚下苏醒。
阳光穿透门檐的冰挂在院墙上投映下斑斓彩虹。我们一众孩童相邀踩着“咯吱”作响的雪去拜年。长辈们用平底箩筐装着花生、糖块,分发给前来拜年的我们。遛完一圈拜完年回家时,身上所有的兜里都是鼓鼓囊囊沉甸甸的,糖块蹭着衣兜发出的沙沙声悦耳动听。路过村口的老槐树,看见几个玩伴正在抽打陀螺。红布绑的鞭梢抽在冰面上,发出清脆的“啪啪”声,惊飞了一群觅食的麻雀。它们扑棱棱滑向远处,翅膀掠过树梢,抖落掉枝头未化的积雪,落在脸上和脖颈里凉丝丝的。随即两手兜成喇叭状,仰天嗷嗷几嗓子,算是对麻雀冲撞的抗议吧。
如今站在超市琳琅满目的年货架前,我总会想起那些蒸笼里冒出的白雾,想起父亲煮猪头时飘满半截村子的香气,想起抢哑炮时冻得通红的手,想起“呲溜呲溜”忙不迭吃水饺时烫麻的嘴。那些年物资匮乏,可年味却浓得化不开。或许就像母亲蒸的枣山,最珍贵的从来不是精巧的造型,而是揉进面团里的光阴和那些被岁月发酵得愈发醇厚的记忆。我摸了摸兜里给孩子们准备好的红包,忽然明白:原来年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个模样,藏在我们为团圆奔波的脚步里,躲在孩子数压岁钱时的笑声中,含在丰盛的年夜饭里,融在每家每户窗户透出的暖光间。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