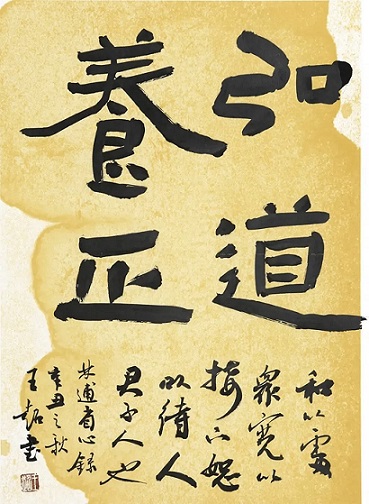岁月里的乡音
回溯往昔,我和姐姐随父母下放,后来还有妹妹、弟弟,最终在梅园村落地生根。为何是梅园村,而非山区或其他地方?这其中,父亲、爷爷奶奶与这片土地的渊源,便是答案的线索。
在《篾箩如车》中,我曾记录下这段家族往事。日军侵华,铁蹄迅速踏入安吉县,县城递铺惨遭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一时间,尸横遍野,鸡犬不宁。父亲和他的姐姐,跟着我的爷爷奶奶,从镇上逃到了这里。梅园村有个自然村叫木橡园,那里竹子漫山遍野,连绵的小竹林中,零星散布着比竹子还高的橡子树。在躲避战乱的日子里,只要听到飞机声,爷爷奶奶一家便立刻从屋内逃进竹林。日军飞机的目标是百姓房屋,躲在竹林里,便多了几分安全保障。
竹子,对于我们祖孙三代而言,早已融入血脉,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宋诗人苏轼在《于潜僧绿筠轩》中曾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竹子于我们,亦是这般意义非凡。
在乡下的日子里,我对竹子的感情日益深厚,甚至将竹子与溪水视作“姊妹”。印象渐深,感慨与赞美也油然而生:安吉的竹林浩瀚如海,被称为中国大竹海。生长在这里的竹子是幸福的,每一滴水,都可能孕育出一株竹;而每一株竹,又让水滴纯净万年。竹子的翠绿,化作会说话的山泉,山泉流淌之处,唤醒每一株竹。竹与泉,似父母,又如兄弟,有着青山的巍峨,亦有绿水的柔情,共同汇聚成这绿色的世界潮流。浙北最高峰龙王山是水的源头,沪上市民逆黄浦江溯源而上,问我安吉的竹子有多少株?我想,竹乡的母亲河西苕溪会给出答案,西苕溪两岸皆是竹,如繁星闪耀长空,又如巨幅宽银幕,每一株竹子都似在踏歌起舞。
小时候听父亲讲,在那段躲避战乱的时光里,他和爷爷奶奶与当地的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成了莫逆之交。正因如此,当父母下放选择此地时,受到了乡亲们热情的欢迎,大家亲亲热热,毫无隔阂。
父亲爱读书,在乡下备受尊重。那时,生产队的社员们文化娱乐活动匮乏。一些机灵的青年社员,知道父亲肚子里“有货”,和颜悦色,且口才极佳,便鼓动大家请父亲讲故事。社员们每日忙于劳作,无论风雨雷电、霜雪交加,都要奔赴田野,一年到头总有干不完的农活。讲故事只能安排在晚上。那时,我常常不知道父亲三更半夜才回家,每次他回来时我早已入睡,都是母亲第二天告诉我父亲“说大书”到半夜才归。这么晚回家,难免招来母亲的唠叨与责怪。
有一次我去生产队,亲耳听到社员们议论父亲:“老汪的‘大书’讲得真好,太精彩了。”后来,父亲心情好的时候,也会把在队里讲的故事内容说给我们听。我这才知道,父亲说的“大书”,素材都来自他珍藏的书籍。比如《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以及各路妖怪,在他的讲述下,个个活灵活现,扣人心弦。尤其是对《聊斋志异》的演绎,那些妖魔鬼怪被他说得出神入化,阴森恐怖,让人感觉惊悚场景就在眼前,毛骨悚然。
父亲不仅“说大书”厉害,还擅长吹拉弹唱。他会拉二胡、京胡,吹口琴;会唱一些越剧、京剧唱段;楷书、行书写得漂亮,钢笔字也如同印刷体一般规整。生产大队成立“文宣队”后,父亲成了辅导老师。队员们常到家里来请教他那些时兴的“戏曲”唱段。父亲识谱,还会谱曲,经常旁若无人地在家里哼唱新创作的歌曲,也不顾是否会给邻居带来影响。有时,他还会让我跟着学唱,教我识简谱,讲解几分之几的调如何“起音”,怎样把握节拍和节奏,这些场景,如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二呀二郎山高呀高万丈,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冈。羊肠小道难行走,抗战交通被他挡哪个被他挡......”我记得,父亲几乎常常拉这首曲子,我也觉得格外动听。父亲边拉二胡,边哼唱着歌词。他告诉我,这首歌叫《歌唱二郎山》,从那以后,我便记住了。许多个夜晚,我都是听着父亲的二胡曲进入梦乡。
农村有着一种质朴而自然的美,这种美似乎掩盖了艰苦岁月的痕迹。父亲把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作对自己的磨砺,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看淡一切。
母亲曾讲过,妹妹还小的时候,经常哭闹,声音尖利。父亲有时为了能尽情拉上一回二胡,兴致正浓时,会把妹妹坐的“竹坐车”放在大门外的田埂上。这种竹坐车,是用毛竹制作的,由当地竹匠专门上门打造。选用的毛竹粗细适中,每一根竹子从粗到细都能得到合理利用。竹子的弯节处,经刀具精心雕琢,“大竹筒”套着“小竹筒”,无需其他材料替代,全是清一色的竹子。就连对接的榫头部分,也是用长短不一的“竹针”,也就是“竹销”“竹榫”固定,严丝合缝。这种竹子制作的小坐具,轻盈灵巧,贴合人体构造;坐具表面保留着竹子的原始风貌,青翠与微黄相间,竹节的粗细、凹凸清晰可见,看着赏心悦目,摸起来清凉光滑。
眼前的稻禾随风摆动,如音乐的节奏般高低起伏。那时,麻雀也欢快地在其间来回跳跃,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妹妹坐在稻田里的竹坐车,宛如一道独特的原野风景。当然,父亲拉着二胡,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这眼前的美好画面。
如今,我从那个村子出来到县城工作,已有40多年。然而,我们一家人对那份乡愁和乡亲们的情谊,从未淡去。
父母在世时,我多次陪他们去看望老乡亲,他们大多与父母年龄相仿,见一次便少一次。
我和村里许多同龄人至今仍有往来。每次回乡下,遇到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们都格外热情。只要在田间地头相遇,他们总会立刻挖些芋艿、番薯,顺手拔些萝卜和菜蔬,还不忘说这些吃着放心,补上一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吃的!”看到他们的笑容,感受着这份朴素与真情,我的心里总是暖乎乎的。尽管我在城里的住处也有几十平方米的菜地,常年栽种时鲜蔬菜,但在乡亲们面前,总觉得他们的“地头货”才是最好的。
麦秸秆
进入霜降节气,大小麦的播种也就开始了。
从村庄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人,大约没有不对麦秸秆怀着一种亲切的。早些年的它,不单是造纸的原料,在它还站在广袤的、充满生机的田野上时,它首先是一株庄稼的脊梁,托举着一粒粒饱满的、圆润的麦子。那真是狂风也刮不倒、折不断的“粮汉子”。它们就那样密密地、无声地立在家乡的大田里,立在每户人家的柴门旁,也立在庄户人那被日头晒得黝黑、却亮着一星希望的心坎上。
麦秸秆的生长,是跟着节气的脚步走的。霜降过后,田地里的晚稻收割殆尽,队员便会扛着犁耙,把土地深耕细耙,整得平平整整,像一块摊开的素帛。接着将精选的麦种均匀地撒在土里,再覆上一层薄土。那细小的种子便在泥土的温床里安睡,不久,嫩芽便争先恐后 地钻出来,先是鹅黄,再是浅绿,最后铺成一片浓绿的绒毯,把田野裹得严严实实。
小时候,我与伙伴们最爱在麦田里奔跑。麦叶划过小腿,带着淡淡的青草香,痒痒的、凉凉的。春风吹过,麦田便起了绿浪,一波推着一波,涌向远方,连带着田埂上的蒲公英、车前草都跟着摇曳。麦秸秆在阳光雨露中拔节生长,起初是纤细的,带着几分柔弱,可过不了多久,便长得挺拔粗壮,节间分明,像一个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它们相互依偎,相互支撑,形成一片密不透风的屏障,挡住了风沙,也护住了地里的墒情。
我总记得那些年月,田是不肯让它闲着的,总要种上两茬、三茬。种春花作物的小麦、大麦,便如同伺候早稻、晚稻一般,是顶顶要紧的事。有了这成片的、金黄的麦田,碗里的饭食,心里的踏实,便都有了着落。对于这日日长在身边的麦秸秆,庄户人早已不是“初相识”,更不是“表象看”了。他们晓得,这看似枯索的秆儿,是能为人类奉献了果实之后,再将躯壳也交付出去的。
麦秸秆的一生,都在奉献。拔节期,它努力汲取阳光雨露,为麦穗的孕育积蓄力量;扬花期,它顶着细碎的白花,在风中传递花粉,孕育希望;灌浆期,它把根须扎得更深,把养分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麦穗,让麦粒从干瘪变得饱满。老农侍弄麦田,也像伺候自己的孩子。天旱了,便挑着水桶去浇水,一勺一勺,浇得均匀;病虫害来了,便背着药箱去喷洒农药,一步一步,走得仔细。他们看着麦秸秆一天天粗壮,看着麦穗一天天饱满,脸上的笑容便一天天灿烂。
每年的芒种,是顶热闹的。昨儿个看着田里还是绿意里透着些微黄,仿佛只一夜的工夫,今天抬眼一望,已是浩浩荡荡的一片金灿灿了。老辈人说,“芒种”也叫“忙种”,人是忙着下种,那有“芒”的麦子,却也到了该收的时候。每一根细如针尖的麦芒,都像是指向人间的、欢乐的请柬;那沉甸甸的麦穗,谦卑地垂着头,却又仿佛喜滋滋地,迎向那闪着白光的镰刀。
收割麦子是老农一年中最忙碌也最喜悦的事。天刚蒙蒙亮,田埂上便响起了脚步声、镰刀碰撞声。大人们头戴草帽,腰系围裙,手握镰刀,弯着腰,一镰一镰地割着麦子。“唰唰唰”的声音此起彼伏,像一首欢快的田园交响曲。割下来的麦子被捆成一束束,码在地头上,像一个个金黄的稻草人。我那时年纪小,便会捡拾散落的麦穗。阳光毒辣,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泥土里,瞬间便没了踪影。可看着那些沉甸甸的麦穗,心里却甜滋滋的。
“春争日,夏争时。”这夏天的每一个时辰,都是金子铸成的,都与那沉甸甸的丰收连着筋、贴着肉。那时的我,也曾跟着大人们在田里劳作过,晓得这收获的艰辛与喜悦。队里的队长,总是扯着嗓子,在田埂上反复地叮嘱:“这麦秸秆,要趁着好天气,晒得干干的,一滴雨也淋不得!造纸厂等着要呢!”
收割后的麦秸秆,被摊在晒场上,接受阳光的暴晒。老农会时不时地翻动它们,让每一根秸秆都能晒得透彻。晒干后的麦秸秆,颜色变得洁白,质地也变得干燥坚硬。孩子们会趁着大人不注意,抽几根麦秸秆,编成小篮子、小蚂蚱,或是做成哨子,含在嘴里吹,发出“呜呜”的声响。
麦秸秆是造纸的好材料,队里将它一车车地送往造纸厂,既是任务,也是集体一项不小的进项。可在农家自己的日子里,它的用处,比起那柔韧的稻秸秆,却要逊色不少。稻秸可以喂牛,可以垫栏,慢慢地沤成上好的肥料。麦秸秆呢,性子太硬,不易腐烂,作肥料也差着一筹。除了偶尔拿来铺铺偏房的屋顶,防些风雨,大多时候,便显得有些无用了。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麦秸秆却另有一种温润的光泽。那便是母亲手编的扇子。
母亲是能将那干燥、洁白的麦秸秆,变出法子来的。她先将它们放在淘米水里,静静地浸泡些时辰。那清水似的米汁,仿佛有一种魔力,泡过的麦秸秆,不仅愈发显得白净,还平添了几分韧劲儿。编扇子的时候,母亲的手指灵巧地穿梭着,那秆儿随着手指曲曲折折地扭出花样来。因了这韧劲儿,它便不易折断,编成的扇面,光洁而平整。母亲是不肯只编一把光板扇子的。她总要让它有些生气,有些看头。
于是,便用些颜料,将部分麦秸染上青的、红的颜色,在扇面上细细地编出些兰草、荷花的样子来。那些图案虽不繁复,却栩栩如生,透着一股朴素的美感。扇柄呢,就用家乡山上新劈的毛竹,削得粗细均匀,再用砂纸磨得光光滑滑,握在手里,有一种清凉的、妥帖的感觉。一个夏天,母亲能编出许多把这样的扇子,自己家用不了,便一一分赠给左邻右舍。夏夜的庭院里,大人们摇着麦秸秆扇子,拉着家常,孩子们则在一旁追逐嬉戏。晚风混着麦秸淡淡的干香,和着蒲扇摇出的凉意,驱散了夏日的炎热,也抚平了一天的疲惫,便成了我童年最安恬的梦。
除了编扇子,麦秸秆在农家的生活里,还有许多细碎的用处。有的会用麦秸秆扎成扫帚,扫院子、扫灶台,虽然不如竹扫帚耐用,却也轻便灵巧。有的会用麦秸秆编成简易的篱笆,围在菜园子周围,防止鸡鸭进去糟蹋蔬菜。甚至在缺柴少薪的年月,麦秸秆也是上好的燃料。把它们扎成捆,塞进灶膛里,火苗“噼啪”作响,燃起熊熊的火焰,煮熟了饭菜,也温暖了整个屋子。那燃烧后的灰烬,还是很好的钾肥,撒在菜地里,蔬菜便长得格外茂盛。
不过,关于这送往造纸厂的麦秸秆,那些年我也耳闻过一些别样的事。说是有些外头来的人,上门收购了队里晒得顶好的干麦秸,运到厂子前,却趁着四下无人,将那冰冷的河水,大瓢大瓢地泼在打成捆的麦秸上。那干燥的秸秆,见了水,便如饥似渴地吞咽下去,分量顿时就重了。虽是烈日当头,表面一会儿就干了,可那水渍,却暗暗地、贪婪地藏在了捆子的深处。过磅的工人,大抵是看惯了这山也似的原料,只粗略一看,便放过去称重了。
我那时听了,心里总有些说不出的滞闷。在这朗朗的乾坤下,竟也有人为了几枚铜钱,行这般鬼祟的伎俩。转念一想,或许也怪不得他们。大约是那厂子“家大业大,财大气粗”,利润高了,便不在乎这些许的损耗,管理上也就松懈了,放任了。这经营上的漏洞,像一道暗处的伤口,恰恰便诱着那些贪便宜的心,往那钱眼里去钻了。更让我觉得可惜的是,那些本应化作洁白纸张的麦秸秆,被水浸泡后,质地变得脆弱,造出的纸也会大打折扣。这不仅是对麦秸秆的亵渎,也是对庄户人辛勤劳作的不尊重。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麦田也渐渐少了。一些土地被流转出去,种上了果树、苗木,或是建起了厂房。曾经一望无际的麦田,如今只剩下零星的几块,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诉说着过往的辉煌。母亲也渐渐老了,眼睛花了,手指也不如从前灵活,再也编不出那样精致的麦秸秆扇子了。那些曾经陪伴我童年的麦秸秆制品,也渐渐被塑料、金属等现代材料所取代,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村庄、麦田、母亲编的扇子,都渐渐远了。只是偶尔在街上,看见那些雪白的、精致的纸页,我还会无端地想起那些金黄的、曾经挺拔在故乡土地上的麦秸秆来。它们的一生,从青青的田野,到沉实的麦穗,再到母亲手中生风的凉扇,最后,或许便化作了这一页无声的、承载着思想的纸。它仿佛是卑微的,却又是完整的。它来过这人间,便留下了它的痕迹。
近些年常回老家,我特意去了曾经的麦田。那里早已没有了金黄的麦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散竹林。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极了当年麦浪翻滚的声音。我弯腰捡起一根散落的竹枝,忽然觉得,它和麦秸秆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它们都从泥土中生长,都有着挺拔的身姿,都在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切。或许,这就是生命的轮回与延续吧。
麦秸秆,这株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庄稼脊梁,不仅承载着老农的希望与喜悦,也承载着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它是那样平凡,却又那样伟大。它用自己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奉献的意义,也教会了我珍惜与感恩。每当想起麦秸秆,我的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暖流,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麦浪翻滚、扇香阵阵的童年,回到了那个简单而纯粹的乡村岁月。那些与麦秸秆相关的日子,如同一张张老照片,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温暖而清晰。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