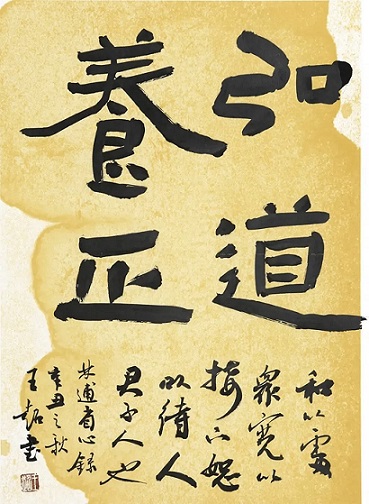大雪节气后的第六日,隐竹山房的围墙已被积雪覆得厚厚一层。青砖黛瓦间白雪错落,就像宣纸上浓淡相宜的焦墨甚是好看。瓦当下悬着剔透的冰琉璃,院中桂树让雪压弯了腰,竹叶顶着茸茸雪帽,在风里簌簌地颤动着。又是一年将要过去。
望着满地皑皑白雪,忽然想起六岁那年,也是这样的大雪天,我跟着母亲去赶嘉县年会。
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格外冷。
母亲是位极能吃苦的人。我总记得她和姥姥坐在房东大门过道里,身下铺张凉席,不管天多冷,不是摇着嗡嗡作响的纺车,便是坐在织布机前哐当哐当地织布。我常绕着纺车跑来跑去,和房东家的小孙子弹琉璃球、滚铁环。
那时全家七口人——父母、姥姥和我们姐弟四个,全靠父亲在银行营业所每月二十几元的工资过日子,紧巴巴的。为贴补家用,母亲便带着姥姥和姐姐纺线、织布、纳鞋底、缝棉袜,做好后拿到集上卖,换些油盐钱。
母亲做针线活是出了名的利落。街坊邻里谁家有喜事要套喜被、做棉袄,都爱请她去。一来她手巧,针脚横平竖直,像用尺子比着纳的;二来她儿女双全,讨个吉利。每逢这种时候,她总带上我。几个婶子、大娘合力缝好大红被子,我便趁机脱鞋爬上被面打滚,母亲轻拍我屁股笑骂,主家老人却呵呵地说:“童子滚一滚,早生贵子哩!”回去时,我常扛着一小包袱主家送的棉花,蹦跳着走在前头。
为赶年集卖个好价钱,母亲总在年前连夜赶工。纺车声、织机声嗡嗡、哐哐响到深夜,我就在这声音里迷迷糊糊进入梦乡。醒来常看见母亲还在灯下缝袜,姐姐已捏着未纳完的鞋底歪在她身旁睡着了。
春节前,雪下得特别大。院子里房东拴在篱笆边的羊,几乎和雪地融成了一片白。
天还没亮,母亲用麦秸火把我的棉袄棉裤烤暖,从被窝里拽出我来穿上。两只提篮装满了新棉袜、新鞋底,临走前她又掀开锅盖,取出七八个热腾腾的白馒头,用洗净的毛巾包好,垫在篮底。然后她一手挽一只篮子,拉着半睡半醒的我,踏进深雪里。
从万张乡到嘉祥县城,十四里路。我们娘俩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时辰。到年会时,街上早已人声熙攘。母亲在角落寻了个空地,摆开摊子。她做的活计扎实,鞋底厚而匀,棉袜针脚密实,不到晌午就卖完了。馒头却不好卖——那时不许私人买卖粮食,被市场工商管理发现要没收的。我们担着心,悄悄地卖,总算没被查到。回程路上,母亲一遍遍念叨:“小来,咱今天可是卖了个好价钱,卖了两块多呢!”
积雪映着日光,刺得人睁不开眼。路过一个卖油条肉盒的小摊时,母亲停下脚步,掏出七分钱,给我买了个肉盒。我捧在手里边走边吃,满嘴油香。母亲看着我笑,那笑声落在雪地里,清亮亮的。
那肉盒的香气,飘过了几十年,至今还绕在记忆的北风里。
崔玉堂,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书友文苑》文学艺术指导、济宁市诗词楹联学会会员、济宁市美术家协会会员、济宁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在中央党校庆祝建党90周年诗歌征文活动中,诗歌《五指峰的记忆》荣获纪念奖。散文《驻村两年与老支书成了忘年交》荣获齐鲁壹点第三届青未了金融散文二等奖、首届“齐鲁金融文学奖”三等奖、第四届“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大赛二等奖。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