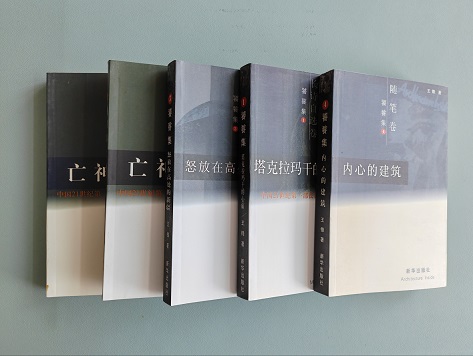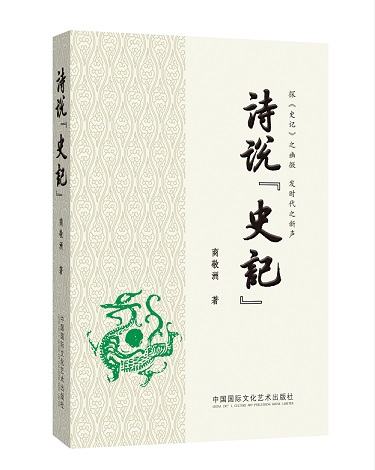读了河南诗人王树立寄来的诗集《树上的天空》(因在外未归,迟读了一年有余),尤其是读了《愤怒》、《老歌》、《在月光里喊娘》、《冬日里的鸟巢》等短诗,心中有说不出的兴味儿。不为别的,就凭这些短诗不“短”,其间所潜藏着的一些“意趣悠长”(胡应麟《诗薮·国朝下》),就值得我品味再三。
是的,我喜欢新诗中有意味、有情趣,或是逐新趣异的短诗或超短诗,怕看一些诗人或写诗者没有敬畏诗歌之心,写出的洋洋洒洒、大大空空的长诗或较长的诗,有些年头了。我觉得经得住时光淘洗的一些经典短诗,大都贵在“虽少而很有意趣”(夏丏尊《文艺随笔》),能使“览者各自得焉”(欧阳修《真州东园记》)。比如:一行诗(即一字诗):“网”(北岛《生活》);两行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三行诗:“静极——谁的叹嘘?//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昌耀《斯人》);四行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断章》);五行诗:“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台湾 夏宇《甜蜜的复仇》);六行诗:“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顾城《远和近》);七行诗:“自从母亲别我永去,/我便不再看她一眼,/深怕那一大滴泪水/落/下/来,/湿了人间”(桑恒昌《中秋月》);八行诗:“阳光在沙漠的远处,/船在暗云遮着的河上驰去,/暗的风,/暗的沙土,/暗的/旅客的心啊。/——阳光嘻笑地/射在沙漠的远去”(艾青《阳光在远处》);九行诗:“打开/鸟笼的/门/让鸟儿飞/走//把自由/还给/鸟/笼”(美国 非马《鸟笼》);十行诗:“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明月如镜 高悬草原 映照千年岁月/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海子《九月》)……
王树立的短诗,可说是既承继了经典短诗之佳妙,又在开拓了属于自己的诗性疆域之时,艺术地展示着各自不同的“意趣悠长”。
“意趣”,鲜活于中心词或关键词里。《愤怒》一诗,有九行。其中心词“愤怒”,为了起到强调某种意思、突出某种情感的反复修辞的作用,竟一连用了七次,在诗中起到了举足轻重作用。诗为:
愤怒的风
啪一声关上
愤怒的门
愤怒的门
啪一声关上
愤怒的风
愤怒的风
愤怒地打不开
愤怒的门
一个日常的所见所闻:大风在随意的关上或打开一扇门,不时地发出“啪”、“啪”、“啪”的响声。诗人王树立在日常生活之中听到了这样的响声之后,为“风”与“门”加进了易表达紧张或不愉快情绪的中心词“愤怒”,并赋予了新的内涵。从而,使“风”与“门”这一有着相互矛盾的对立物(表意的物象)产生了新的意趣(即意象所含)。我们若是将此情此景自如地扩展开去,定然会发现在芸芸众生、日月星辰、宇宙天地、万事万物之中,何止是“风”与“门”有这种相互抵触、撕扯、仇视,甚至是你刀我剑、互不相让(即“关上”与“打不开”)的现象啊!由此看来,此诗的引申义、象征义可谓应有尽有。
像“愤怒”一词的多次连用的反复修辞手法,在《你静等花开了吗?》一诗中也有“跨时空”式的渐进式发挥。其“静等花开”,是中心词(即动宾短语),一连用了七次。如“没人静等花开就下课了/没人静等花开就放学了/没人静等花开就幼儿园毕业了/没人静等花开就小学毕业了/没人静等花开就中考了/没人静等花开就高考了/静等花开”,为诗尾三句所潜藏的“多么浪漫耐心的一生的爱的教育/谁等到花儿也谢了/空悲切”所潜藏的意趣作铺垫。于是,《你静等花开了吗?》里的“花开”与“也谢了”、人的某一阶段与人的一生似乎都是在“静等花开”中度过的。诗人王树立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教育工作者,对于所教育的学生而言,每一次授课是“静等花开”,每一学期是“静等花开”,每一学年、每一届是“静等花开”,不想在“空悲切”(即岳飞《满江红》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婉惜之中看到某一朵花的“也谢了”。所有这些含蕴,可视为“多么浪漫耐心的一生的爱的教育”之爱心、大爱之心与期待之心的一种艺术性呈现。
《玉兰花开》,用了一个关键词“消费”:“玉兰花开了/今年开在3月15日 消费日/它在春天里消费自己的光阴/我们也在春天里消费自己的时间/他在消费自己春天的时候/开出了生命的花朵/我们在消费自己春天的时候/像玉兰花开/怒放生命吗?”诗中,只借“消费日”的特定时间,在一种“花”与“人”的比较之中,让关键词“消费”产生了味外味的意趣的同时,礼赞了“开出了生命的花朵”之玉兰花。进而,在一种追问里暗寓了没有像玉兰花一样“怒放生命”或“消费”生命的众生,给人留下了无限量的思考。
《老歌》里,一个关键词(“寻找”)与三个意象(“一片月光”、“一杯咖啡”、“一把刀子”)组合在一起,产生了不一样的意趣:
一片月光
一杯咖啡
一把刀子
寻找熟悉的伤口
把往日的鳞片
一一剥落 但不滴血
让疼痛重新长成一条鱼
穿梭在你的前生
也鲜活在我的来世
夜来,在餐饮处。外有“一片月光”,内有“一杯咖啡”“一把刀子”(食主与肉食等物被悄悄地搁置一边)。这里所提到的三个物象“月光”“咖啡”“刀子”,一经被诗人赋予了人之情怀,便在“寻找”的引领下,“寻找”一道“熟悉的伤口”,生发出独特的意趣。而后,在通感手法的艺术运作中,“让疼痛重新长成一条鱼”,并使之前生来世自由地“穿梭”。此时,我们若是再回过头来看看诗题《老歌》,不难发现诗人的真实用意:我们这些尘世之凡夫俗子,总是在不经意间重复着“老歌”一样的腔调:在受伤后“疼痛”,在“疼痛”后享受;在享受后受伤,在受伤后享受……
“意趣”,蕴涵在比拟、比喻里。《项羽!毛鸡蛋》(题记:没孵出小鸡的蛋,鸡雏成型,残忍地煮成五香蛋,许多人爱吃):
英雄的梦想
没啄破历史的蛋壳
却变成一道菜
任千古评说
热爱
摒弃
读过白居易《琵琶行》的诗前小序与诗,我们知道小序与诗是息息相关的:先看浓缩了诗中大意的小序,也就先睹为快了。诗人王树立的《项羽!毛鸡蛋》是首仅有六行的短诗,其小序的客观介绍,亦起到了更好地理解诗中之“项羽”与“鸡毛蛋”相比拟的意趣。这样,历史人物——“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夏日绝句》)的英雄项羽与未长成小鸡,成为“许多人爱吃”的毛鸡蛋,也就增添了特有的修辞效果:项羽与毛鸡蛋,尽管有梦想,却难以“啄破历史的蛋壳”,活出“唯我独尊”的一世风采。反而“变成一道菜”,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评说”“热爱”“摒弃”的不老的话题。从诗之主旨可以看出,诗人采用了反讽与揭蔽等艺术手法,使其挥之不去的意趣,自如地引发人们的警醒与深思。
《月亮》一诗,共六行。前五行写“月亮”。如:“一颗不朽的诗魂/有冰冷的温度/也有热烈的向往/它的冷热程度/全凭自己的阴晴圆缺”。后一行写:“当然,也少不了那个望月的人”。诗中,司空见惯的“月亮”,被诗人喻为“一颗不朽的诗魂”,也就具备人了的情感:有“温度”、“热烈的向往”与能用“阴晴圆缺”来调节的“冷热程度”。诗人这么写人性的“月亮”,无疑的,是为了引出最后一句“当然也少不了那个望月的人”。这样,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诗人先写“月亮”,而“月亮”有人之性格特征;后写“望月的人”,而“人”与“月亮”相知相亲。如此一来,“人”“月”不分,已两情合一了。
《时光三剑客·一、光阴书》(组诗)的几个“用常得奇”的喻体(“大针”“小针”“ 绣花针”),与三个个名词(“年”“月”“日”)排列在一起,在一种不动声色之中向我们传递着极为丰富的意味与情趣:
年 大针
月 小针
日 绣花针
在时间的针鼻里
日月穿梭
把日子串起
年 出版
月 发行
日 签名
意趣,扩缩于虚实之间。我们知道,写给母亲的诗数不胜数。譬如上文提到的《中秋月》,是著名诗人桑恒昌怀亲诗的代表作:“自从母亲别我永去,/我便不再看她一眼,/深怕那一大滴泪水/落/下/来,/湿了人间”。此诗仅是一个复句,分七行,全诗三十一字。可以说这个复句的容量超大,于虚之实之间,将“中秋月”喻为“一大滴泪水”,极显思母之情真意切、哀伤无限。王树立的《在月光里喊娘》,与桑恒昌《中秋月》的开头尽管有点相似(前者“自从母亲别我永去/我便不再看她一眼”、后者“自从娘走后/我就不敢看月亮”),但在接下来的诗行里却不似桑恒昌将“月”喻为思念母亲的泪水,全凭虚笔托情的手法,将“月亮”当娘“喊”——“所以每一次抬头看见月亮/我都忍不住轻轻喊一声——/娘!我在这里”)的意趣,凸显了另一番催人泪下的思母之情,有“无理而妙”、余味绵长的艺术效果:
只要一抬头看月亮
我就看见娘的泪汪汪的眼
但有时 我还是忍不住想看一眼月亮
我知道 娘的魂魄夜夜都站在月亮之上
四处张望——
她的儿女今夜在哪?
所以每一次抬头看见月亮
我都忍不住轻轻喊一声——
娘!儿在这……
同是忆念母亲的《妈妈的花儿落了》一诗,亦是虚实结合之作:“妈妈的花儿落了/我家的梨树开满了花/妈妈的花儿落了/我家的梨树叶开始花落/雪白雪白的梨花飘落满院/很痛恨痛的妈妈越走越远……”
《冬日的鸟巢》,在实写有“鸟巢”的大树上“所有的果子和叶子飘落以后”,艺术地虚写着“我是你唯一的眼睛和嘴巴”,显得妙趣横生:
在光秃秃的大树上
眺望
乡村啊
当所有的果子和叶子飘落以后
我是你唯一的眼睛和嘴巴
在枝头把日子叫醒
擦亮
当然,王树立诗集《树上的天空》中的若干短诗,包括此文中所选的短诗,并非都做到了“意”、“趣”相携,且逐新趣异。但从整体上看,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伸出理智的大拇指,对着诗人王树立的短诗说一声,够味!
2021年10月29——31日于鄂州鸟缘居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