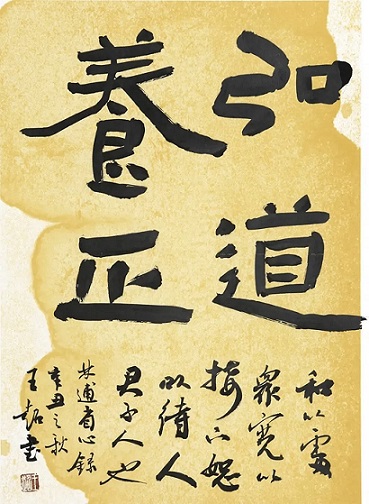在文化市场的某个角落,我偶然遇见一只带扳的白瓷杯,杯身不及巴掌大,画工却精妙到让人屏息。青绿墨色晕染的竹林间,一位戴草帽、穿降色上衣浅色裤子的书生骑着黑驴缓步前行,另一人用竹竿撅着行囊,急急跟随。整幅画面不到指甲盖大小,却将旧时举子赶考的神态、动作乃至心境刻画得活灵活现。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一行小字:“丙午年作”——那是1906年,科举制度刚刚废止不久,这只杯子仿佛成为那个千年赶考时代最后的微缩注脚。
看着它,我不禁想起“骑驴赶考”这个带着书香与尘土味的历史故事。
驴,举子的“标配”
在古代,马是高贵的象征,价格昂贵到令人咋舌。贞观年间,长安一匹马可值十几两黄金,相当于今天的几万元。穷书生哪里骑得起?于是,驴成了平民和落魄文人的主要交通工具。唐宋时期,驴甚至被称为“劣乘”,但在举子眼里,它却是通往仕途的忠实伙伴。
更有趣的是,为防止攀比,显示平等,唐懿宗曾下过一道“奇葩”圣旨:举子赶考一律不得骑马,改骑驴。结果,一年竟有三千考生骑驴进京,蔚为壮观。有人还为此作诗调侃体形魁梧的举子郑昌图,说他骑驴的样子滑稽可笑。然而,郑昌图不仅没被嘲笑影响,反而高中状元,可见“骑驴”与“成败”并无必然联系。
驴背上的诗与故事
骑驴不仅是赶考,更是灵感与际遇的温床。贾岛骑驴入京,在驴背上推敲“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用字,竟与韩愈相遇,结成诗友;又有一次,贾岛深秋在长安街上骑驴慢行,看到纷纷落叶触景生情,吟出一句“落叶满长安”,忽得下句“秋风吹渭水”,正暗自欢喜间,不知不觉中又一次冲撞了京兆尹的车仗,此时的京兆尹是刘栖楚,刘栖楚一气之下把贾岛关了一宿。这便是“推敲”的由来和驴背上的文坛佳话。
到了明代,京城的“赶驴桥”更是见证了成千上万举子骑驴往返贡院的盛况。那时的驴蹄声,仿佛是那个时代最密集的节拍。
正如民间传唱的举子心声:
——骑驴赶考梦马还
青灯熬瞎眼,馍硬硌牙关
赶考骑瘦驴,嘚嘚叩山川
驴脾气,倔上天,偏啃路旁甜菜田
“老兄快点走,中榜给你配金鞍!”
泥坑水洼颠又颠,诗囊甩落散云烟
满地摸字像摸鱼,蛤蟆噗通笑我癫
昨夜梦戴花,打马御街前
今早驴背晃,剩三文钱叮当响耳边
莫笑书生穷,怀里揣月圆
驴蹄嘚嘚苦也甜,来日马蹄踏金砖!
时代变了——从驴马蹄声到高铁呼啸
古时官道每相隔约三十里一个驿站,送公文时骑手是驿站换马,接力奔驰。一天跑下来,就是人们常说的“快马加鞭,日行三百(里)”,如北京一沧州一德州一济南一兖州一徐州,其间距大约是三、五百里,是按一天行程设置的。一般情况下到了这样的地方,就可停马休息。若公文包写有“快马驰报”,就连续要换人换马,继续驰骋,直至公文到达。
而今天,我们只需几个小时便可跨越曾经需要数日甚至数月的距离。高铁飞驰,飞机翱翔,甚至宇宙飞船正将人类的足迹伸向星辰大海。
从驴背上的书生,到高铁车厢里的学子,交通工具的变迁不仅是速度与舒适的提升,更是知识与机遇的传播方式的革命。今天的考生,不再需要担心驴子疲惫或路途遥远,他们可以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安心备考,然后在短时间内抵达考场,这是古人难以想象的便利。
回望骑驴赶考的岁月,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艰辛,更是坚持与希望。那是一种在有限条件下依然奋力前行的精神。手中的白瓷杯作于1906年,正处科举终结与新时代教育萌发的交汇点,它凝固的不仅是骑驴书生的形象,更是一个漫长时代的缩影。而今,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交通与信息条件,更应珍惜这份便利,将古人的进取心化为今日的行动力。
未来,或许我们会坐着高速飞船去“赶考”,甚至在月球或火星设立考场。但无论科技如何进步,那份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执着,始终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驴蹄声远,高铁声近,唯有那怀揣“月圆”、奔赴前程的心,从未改变。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