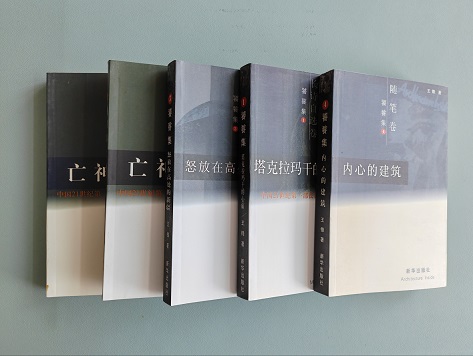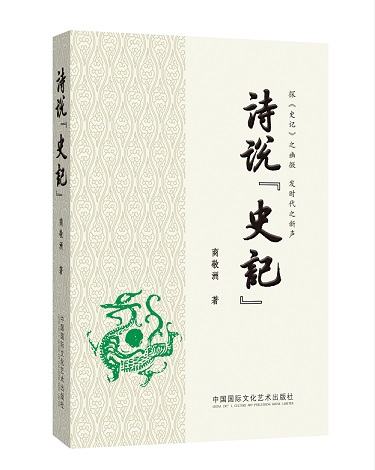金浪的《再造传统:战时美学的文化想象(1931-1945)》(以下简称《再造传统》)出版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前夕,将“战争状态”下中国美学的丰富图景再次带入读者的视野。近年来,抗战时期文学书写和作家精神历程备受学界关注,涌现一大批富有新意的成果,该时期的美学研究相较之下却颇为寂然。究其原因,人们一面习于在“启蒙”视野中理解美学这一“舶来品”,一面又普遍将“中国美学”视为更为晚近的产物。《再造传统》以朱光潜、宗白华、李长之三个生动的个案有力证明,“救亡”时代的美学话语不仅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现实使命,更奏响了绵延至今的诸种讨论的“前奏”。在此意义上,《再造传统》并未止步于战时美学的历史描述,而是通过重审特殊时期的“美学中国化”和“中国美学化”,为理解中国美学的知识生成打开了全新的空间。
作为文化抗战的中国美学
1937年,朱光潜在四川大学演讲时强调:“在战争中两国互相抗衡的不仅是枪炮,尤其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此言恰可代表三位知识背景各不相同的美学家在抗战时期“再造传统”的共同动力。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美学怎样与“民族精神”相联结?“民族文化”复兴的道途中,美学处于何种位置?这是时代赋予所有美学家的共同课题,也是此书强调“战时”视角的焦点所在。
通过三位学人战时迁徙和社会参与的全景回顾,《再造传统》将书斋内外的美学论著和文化实践勾连起来,引领读者回到文化抗战的紧迫氛围中,一同领略美学话语演变背后炽热的现实关怀。此书讨论的对象中,既有以朱光潜《诗论》为代表的学术经典,亦有如《谈修养》等美学家撰著的面向社会的通俗读物,还包括李长之文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的“宣言”体文章。无论是透视美学专著版本变迁中的幽微心路,抑或是洞察时论文章中潜藏的美学思维,都成为此书重探战时美学文化想象不可或缺的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特别关注美学话语的“内部运动”:战时的需求带来了美学话语朝向传统的整体性“转折”,但这绝非偶然的突变,而是依赖美学家对不同资源的吸收、融汇与转化,其中存在待仔细辨认的历史逻辑。正如本书绪论提到,晚清以来王国维、梁启超、梁漱溟都曾试图“将美学视野运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只不过这一面向在以“社会改造”为主潮的时代并未充分开展。直到战时,现实的重任才让中国美学的文化建构取得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当文化抗战以胜利作结,美学家们的足迹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持久影响。关于美学“中国性”的讨论已被激活,“再造传统”的努力在几代美学家中延续,彰显着中国学人追寻文化主体性的信心与风采。
重焕生机的传统
《再造传统》中三位美学家的学术道路皆在以“反传统”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之后展开,却在战时以“再造传统”为己任。若不能充分意识到“再造”与“恢复”之差别,便注定无法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该书绪论援引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指出,传统“始终处于未完成的开放状态”,传统之所以能够乃至必将被“再造”,正以“未完成性”为根基。战时美学充分发现且利用传统的“未完成性”,在传统与当下之间建构起紧密的联系,才让传统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潜能,同时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为了甄别战时美学“再造传统”的多元路径,该书对一系列首次被运用于中国文化的新概念、新范畴进行了“知识考古”。如在第三章中,作者发现“写实”“浪漫”“古典”三个范畴共同构筑了李长之重释传统的思想体系。它们并非来自传统本身,而是源于其“文艺复兴”构想的西方“模版”,其中18和19世纪之交德国思想家的启发尤为关键。李长之把孔子和屈原分别奉为“古典精神”和“浪漫精神”的代表,并质疑“五四”运动时期知识界缺乏对“孔子的真精神”的认识。饶富意味的是,李长之批判今文经学“迷信”、古文经学“支离”、宋儒“空谈义理”,这与“新文化”主流的思路并无二致。而他所看重的“深厚”“热烈”的“真精神”,实质上就是理想主义、非功利的“古典精神”。这种被建构的“古典”充满了“现代”基因。
除新概念、新范畴外,诸多“古已有之”的概念之“新生”也在该书中得到细致辨析。由于这些概念的“现代版本”已经被学界广泛接纳,人们往往对其含义的古今之别习焉不察。追问“新生”所依赖的方法论基础,是该书为理解“美学”与“中国”之磨合所作的又一贡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第二章对宗白华战时美学中“意境”概念的探讨。作者指出,宗白华之所以“打捞”出这一概念,乃是为了勾勒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的差异,并从中提炼出具有超越意义的艺术原理。经过重构的“意境”概念具备更强的开放性、包容性,成为宗白华构筑“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的重要基石。
美学概念体系的创造性重构必将引向传统的整体性重估。从宏观层面揭示诸种“再造”路径的价值和限度,是本书“知识考古”之指向所在。例如,作者从朱光潜战时纷繁的论述中抽绎出“以情释儒”这条核心线索,并将其放入近代中国“儒家审美主义”的思想脉络中确证其“前所未有的高度”,便点出了其“再造”思路的开拓性意义。战时美学家对“何谓传统”“传统的长处何在”进行了富有理论勇气的创造性回答,为今日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留下了值得总结和借鉴的经验。
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的“古今”问题始终与“中西”问题密不可分。抗战时期的文化重建,同时也伴随着知识人对世界的重新认识。该书以普遍性与特殊性这对概念探察战时美学的思想构造,凸显出战时美学的文化政治意涵。战时美学家之所以不满于单向度的模仿和转述、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龃龉分外敏感,又对中西艺术、哲学的比较用力甚深,皆与嵌入美学“地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辨紧密相连。
纵观全书,普遍性与特殊性并非美学家被各自贴上的标签,作者力图呈现的是二者的转化、对抗关系及“交错状态”。中国现代美学的关注点从美的普遍性逐渐转移到特殊性,包含着抵抗西方霸权的努力;而新的文化想象成形的时刻,便是特殊性向普遍性迈进的起点。如该书绪论所言,中国知识人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综合,也是德国等后发现代国家曾走过的道路。作者强调,在美学学科逐渐“中国化”的同时,中国也在战时走向了“美学化”——美学话语催生了对中国文化特质的新认知,“美学中国”的知识形态随之浮出地表。三位美学家的“传统再造”,既折射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又深化了“中国美学”和“美学中国”的相互联结。
抗战即将结束之际,宗白华曾言:“我们并不希求拿我们的精神征服世界,我们盼望世界上各型的文化人生能各尽其美,而止于其至善,这恐怕也是真正的中国精神。”这清晰展示出“传统再造”所包含的未来向度:美学家并非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展开想象,而是通过重新认识本国文化来思索中国可能为全人类所作之贡献。“传统再造”表面上以中国为对象,实则蕴含对人类文明前行方向的反思。作者重读宗白华的“中国精神”论述发现,美学家普遍意识到中国和西方各自“往哪里去”是无法分割的问题,偏于“艺术”与“科学”一端都不足以解除西方文明给世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宗白华高远的文化理想并非孤例,显示着中国知识人从被动“融入”/“适应”到追求“改造”/“引领”世界潮流的蜕变。
受益于“再造传统”的战时遗产,今日“美学中国”正如三位美学家所期许的那样,在民族复兴的道途中绽放光彩;“中国美学”知识体系的构筑亦成果丰硕、日趋完善。该书的历史回顾不仅还原了影响深远却未被充分观照的思想历程,更为思考当下学者的处境与使命提供了鲜活的参照和启示的源泉。
(作者系重庆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