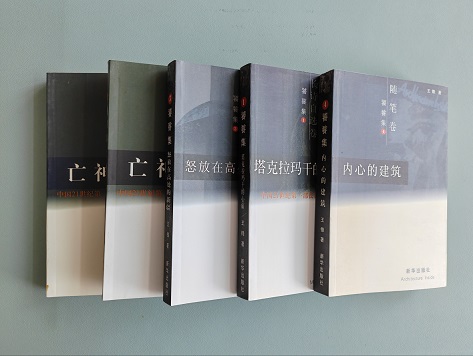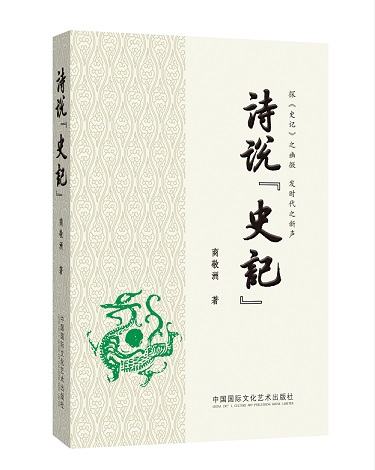1 笔墨运行的缘聚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书法世界就是“阴阳相生”的哲学道场,无论是一幅字,一个字还是一个笔画,它的运行始终存在于对立统一的道法之中。每个笔画里都藏着最朴素的辩证法,就像中国人骨子里的“太极”,阴阳捭阖在笔墨的运行之中,意境被体现得辽远深沉,研究它就能获得传统道德的美感和人生智慧的哲理。有了这些丰富的知识做基础,根就会扎得深,枝叶便蓬蓬勃勃喜悦旺盛。
我们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寻找中国书法与自然的密切联系,打开老祖宗的人生活动,很快就能发现,笔画的运动之态、形状、仰卧、呼应都与外在自然事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原始人的击石取火到岩画的相形文字产生,都存在于事物的发展变化之中,变,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所以我们在讨论书法技巧时一定不能忽略了这个变化,如果你能把事物变化的深刻内涵和外延掌握在自己的心中,那么你对书法的创作就可以攀登抵达高峰了。
从书法的“提按”打开笔毫而论,运笔是最直观的阴阳变化,它就像一轮红日滚动在洁白的宣纸上,发生着墨韵于笔法的万千变化,这种变化看似偶然,实则是对事物认识的长期积累;提笔时笔尖触动纸面,力量开始有了变化;墨色浅淡如“虚”,如月光洒在水面,留白处藏着无限想象;按笔时笔锋沉着纸面,力量渐渐体现,墨色浓重如“实”,像黄昏压在大地,力透纸背处见落日的力感。在一字一行里提按交替出现,虚实相互映衬;方显一幅作品的灵动,这种灵动常常与自然的生命状态联系的很紧;你看笔墨的虚也不纯粹为“虚”,虚中藏着力量的质感;实也不绝对为“实”,实中裹着气韵的流动;如老子曰:“有无相生”的变数。书法的魅力就在于提按的运行之中获得变化的平衡,缺了提则不爽,少了按则不快,所以提按一直是古人研究书法理论的重要环节也是变化的良好开端。
是的,轻重是由人来把握的;一个字的轻重根据书写者的情感和当时环境而生发的,如颜真卿的字,竖画皆用浓墨写得粗壮挺拔,能撑起一片天空;笔墨里藏着无穷的力量;董其昌的字偏爱淡墨,行笔如行云流水、轻歌曼舞,在蜻蜓点水里又隐藏着实实在在的变化机缘。轻和重不是孤立的,浓和淡是相映衬托的一对彼此,淡墨若没有浓墨的锚点,会显得漂浮无根,浓墨没有淡墨的衬托会显得沉闷压抑;就像“存在”总要在“有和无”的关联中显现自己。
2 笔墨形态的变化
自然间的规律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智慧源泉,只要我们细心地去观察事物的变化就能发现一种规律,比如书法中的“藏鋒与露鋒”就是从自然间发现的一种规律:如种子埋进泥土里就能生根发芽,破土而出。而书法中的藏鋒与露鋒就是运笔中的一对矛盾:藏锋时笔锋内敛,像种子埋进泥土,蕴发着万物迎春的姿态,等待绽放;又像做人踏实不虚妄,诚实得让人有种敬畏之感,悠然而生,把锋芒藏在四季里等待着交换。露锋是笔锋外现的一种技法,似利剑出鞘,斩钉截铁,如放箭,不拖泥带水;收笔,像做事果断不含糊,势不可当,把力量显现在明处。如颜真卿的字多藏锋,透着“外圆内方”的宽厚;米芾的露锋,带着“狂放不羁”的洒脱;但无论藏与露,都不是绝对的,藏有露的玄机,露有藏的奥秘,就像人生的“藏巧于拙”与“寓清于浊”的道理,总是在对立统一中存在着变化。
“刚柔”也是书法的一对矛盾,其实书法所有的技法都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而后,熟到形而上的神圣高度进入道。刚则刚易断:柔则柔难立,就像太极,黑中有白,白中有黑的两个小气孔。楷书,横平竖直像君子无灵活应对外部世界,失去了立身处世的原则,笔画公正的失去了涵养。行书的牵丝连带如“柔”缠绕着一个顺势而为的中心,像一股涓涓之水,行而不止,流而不浑。楷书的“捺笔”收尾时略轻提,刚劲中藏着舒展;行书在“转折”处暗使顿笔,灵动中藏着骨力。这种“刚柔相济”的运行规律,恰似阴阳共生:没有不变的生硬,也无停止的柔软,笔墨在“刚与柔”的运行中写出最鲜活的生命笔画和透出自然之道的精神内涵。
书法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这正是文脉深处的哲学密码,让笔墨不仅成为艺术的生命营养,更是解读人生的生活哲思。
3 笔墨诠释的有无
有无是万象变化的母体,有是无的开始,无是有的变化,二者互为推动生发着这个无穷无尽的大千世界,人类就是从这个无穷无尽的变化中不断地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掌握事物变化的因果。书法就是这个变化中的理论体验和规律展现,比如,浓淡与黑白的交织,恰是阴阳互动的哲学存在,也是辩证的笔墨在书写中化作可感知的云雨,能传递的情感,会说话的音符,让书法成为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哲学镜像”。
玄妙,却常常出现在一种极致的存在之中“无”是留白的玄妙之处;笔画似断非断,像“非存在”的虚空却暗藏着无限的张力;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怀素写草书时,长撇末端常出现飞白,墨迹渐淡却盘绕着如游丝,看似“无墨”,却让人感受到笔锋继续延伸的动态感;章法中的留白如“无”,字之间的空隙,像“非存在”孕育沉默的想象;一幅作品若塞满笔墨不留空白,像窒息的房间,而留白处则如开窗透气,让观者的目光有停留安放之处,思绪有延伸的意境。这“无”从不是“空”的,而是“有”的延伸:飞白的“无”是笔墨意境的拓展,正如黑格尔所说“无是存在的否定,却与存在不可分割”。这种“有无相生”的智慧,在书法里化作无限的意境:古人说“计白当黑”,正是把“无”当作“有”的笔墨语言来认识,就像生活中“说出口的话”是有,“没说出口的情”是无;“做到的事”是有,“等待的时光”是无,两者共生才是有趣的人生,开一间房子肯定有一种创造,等待春天的到来。
4 笔墨底层的逻辑
人类在不断地总结经验中,从书法的书写中得到了智慧的启发,不断地将事物的形象、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融入汉字的书写中;书法便在实践的劳动中诞生出智慧和逻辑,它从用力的轻重、缓急,着色的浓淡展开书者内心的生活感悟而产生了艺术的表达;书法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洋溢着蓬勃生机的生命往来与语言传递,它的底层逻辑早已融入世界的物理联系,如速度的节奏、音乐的韵律、色调的强弱、劳作的质朴、距离的远近等,看似无关,却都于运笔有着隐秘的“关系”,在“力与节奏,情感与着色,山水与形态”的公共通理中显露着文脉的普遍性和规律的一致性。
在我们的生活中,张力与笔墨的遒劲是同一种语言:篮球运动员上篮时,手臂舒展如“长撇”,腾空扣篮的瞬间发力如转折处的“重按”;身体在空中跳跃的平衡感,恰似书法中“中锋行笔”的稳与“侧锋取势”的灵活统一;舞者的旋转、收放,裙摆扬起的弧度飞白,落地时沉稳的“顿笔”,那种运动中求静的控制力,与书写时笔走龙蛇的张力如出一辙。这些运动的“力”,和书法笔画里的“提、按、顿、挫”本质相通,都是蓄力、着力、发力、收力、放力的节奏,是身体与力量的默契对话于书写者的内心表达。
音乐的节奏与笔墨的韵律是同样一种生命的呼吸;古琴的“泛音”如书法的素笔,余韵像留白;鼓点的碰撞如“奋笔疾书”,铿锵有力的挥舞折叠如沉实的落笔。一首乐曲的“强弱缓急”,对应着一幅书法作品的“疏密虚实,浓淡远近”的哲思,让旋律有了呼吸起伏的空间,笔墨因节奏变化有了生气。古人曰“书法如乐”,因为两者都靠“节奏”传递情感,没有节奏的字是堆砌的笔画,没有节奏的乐是杂乱的音符,这共通的“韵律感”,正是底层逻辑的显现。如工匠打铁时,铁锤落下的“猛力”如“竖画的挺拔”,都是力由身发“手随心动”的自然流露。 书法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专属技巧”,而是万物通用的力与节奏的哲学展现,都能在笔墨里找到共鸣;这种“万物皆缘”的关联,让书法不只是案头的艺术,更是连接社会实践与创新的桥梁,读懂了他,就能理解书法为什么能跨越千年而依然是最打动人心的根本所在。
5 笔墨形而上之美
其实,书法的理论说到底统统归于形而上之美;是的,书法是直抵书写者心灵的东西,是书者灵魂深处进行跨越时空的一次神秘交流,是通过笔墨感受其精神世界的气象与风骨在生活中的创造性与传承性。是体现书法至高境界、超越视觉形态的“形而上”的道统之美。它不仅仅是线条、结构与章法的精妙组合,更是书写者精神世界的真诚投射与生命气息的纯粹流动。这种内在的美,来源于作者自身的内在的陶冶与道德修养。首先其心缘有着强大的正能量,在文字的书写中体现为气韵生动的节律运行,在文采飞扬的墨色里顿悟枯润浓淡、运笔缓急,顿挫留白与着实共同构筑作品的生命力与节奏感,使其行云流水般地富有动态的韵律。其次,书法能够营造出深远的“意境”美,通过虚实相生的布局和刚柔相济的笔力,引发观者的联想,或感受其豪迈与奔放的激情,或体会其宁静与致远的禅意。古人云“书为心画”,正是因为书法最终指向的是书写者的人格展现与道德升华,它将无形的精神气质,凝结为作者内心有形的笔墨痕迹,使观者在欣赏笔墨流动之美的同时,能与书写者的灵魂进行诗意的道德对话和神采的韵味契合。一幅好的书法,你能感受到一股生生不息的流动感。
古人说“书为心画”,意思是书法是书写者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一个人学识、修养、性格甚至品质,都会不自觉地融入到他的笔墨之中。所以,欣赏书法,也是在与古人进行一深邃的文化交流,感受他们宽广的胸襟与高洁的风骨和深厚的文学底蕴。王僧虔明确指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 他认为,由形态所传达出的“神采”比字的笔画、结构等“形质”更重要。所以能得到形而上的笔墨感受是书者平生的快慰。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