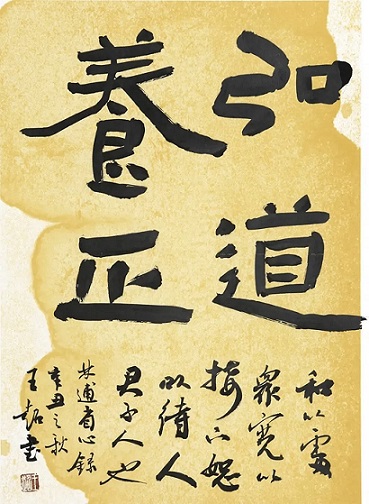一
一大早,天上的太阳就炙烤的马路像蒸笼,大日头下急急走在南粤特区大街上的诗歌,本来上街是给老家里的父母亲寄钱的。十字路口等绿灯时,见人行道那头红润脸膛穿印着“下岗创业”桔色T恤胖胖的美莲嫂,在马路对面大声吆喝,“快来看,快来买呀,今天的早报有大好消息,写诗得奖还能落特区户口喽。”
乍猛一听,诗歌似乎觉得是那么回事,又觉得耳边的“写诗得奖落特区户口”像是“嘁哩隆咚戗”,心里便埋怨美莲嫂,下岗都卖几年报纸了,说不好普通话老还操着像吃了烫洋芋舌头短了半截的粤语。
想什么来什么,许是美莲嫂早知道诗歌第一句吆喝没听清,第二句又飞过了马路,这回听清了,美莲嫂的吆喝不光让诗歌停下了脚步,还把汗流浃背的诗歌,像是吆喝里边有条缰绳,把诗歌牵牛般的牵过热气蒸腾涂着斑马线的柏油马路,牵到了美莲嫂面前。
诗歌低头盯着美莲嫂让汗水浸的像沾满了露水亮晶晶红苹果般的脸庞,问:“今天早报有写诗得奖落户口的消息?”
低着头忙着边吆喝边给围拢的买报人拿报纸紧着收钱找钱的美莲嫂,抬头看是诗歌,高兴的高喉大嗓说:“大诗人,你可来了,我正准备卖完这几份报纸,给你送报纸去呢。”
热气腾腾被汗水浸得头发湿漉漉的美莲嫂,嘴里不停的说,手里飞快地给诗歌递送过来早报、日报、商报、都市报厚厚的一沓报纸,“大诗人,快拿去,快去看,显摆你本事的机会来了。”
诗歌把报纸钱递给美莲嫂,她不接,让美莲嫂左一句大诗人,右一声大诗人,推搡着他,数算着他,在买报的,钉鞋的,卖冷饮、水果的,还有交通岗亭警察关注的,艳羡的,怀疑的,不冷不热各色目光的注视下,把他逼出了人群。诗歌讪讪的找了个阴凉地,把手里几张报纸,挨着看了看,“写诗得奖落特区户口”的消息,几家报纸像是春节贴的对联有上联就有下联,不光份份不拉挨着个的登载,“写诗得奖落特区户口”的消息还全给套了红,显目的让诗歌眨眼便把登载消息的这些报纸一、二版飞快地浏览了一遍。
原来是为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繁荣打工文学,关注农民工”,南粤特区劳动局和《小草》诗刊联手,把外来务工人员奉为主角,要举办特区首届外来务工人员诗歌大赛。
特区诗歌大赛奖项分为一、二、三等,分别给获奖者奖最高十五万,最低五万的现金,还统统给得奖者落本市户口。更让诗歌瞠目结舌的还有唯一特等奖,不是奖现金,而是给奖一套八十平米的房子,外加按特殊人才引进到《小草》诗刊上班。
别说其它奖励,光八十平米的房子,在诗歌打工的这个位于南粤的特区城市,此刻儿看报纸的城乡结合的位置也要五十万了,更别说在市中心了。
八十平米房子“痒痒”的能把诗歌的心勾出来,当然,现实里心没有从肚子里爬出来,只是让诗歌打心底悠悠产生出一股“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豪气。心里充满了阳光敞亮无比。
一转眼,刚才还让豪气鼓的像气球一样的诗歌,又“哧哧”地泄了气,泄气的原因:报上刊登的外来务工人员诗歌大赛简章里规定了,参加诗歌大赛外来务工人员的户口必须是农村户口,“是农民工,写农民工”。“让广大农民工文化成才诗歌成才。”
诗歌的户口是城市户口,他哪有资格参加诗歌大赛。城市户口的诗歌是城市人,大赛干他鸟事?
报纸白纸黑字还说:“该大赛开辟了农民工进城务工成才的新渠道。”
刚才,还心里像当头“蓝格莹莹的天”的诗歌,霎时眼泪便眼看着要流出“清粼粼的水”来,就差让“羊肚肚毛巾”把自己勒死了。
诗歌是唱“信天游”和“花儿”还有“走西口”这些民歌长大的,按时髦的说法,他的老家乃至整个西北都是这些民歌的原创地,刚才,不知存在肚子哪个旮旮旯旯的几句“信天游”让诗歌随口就苦焉焉地哼出了嘴。
诗歌是城市人。不是农村人。更准确地说,诗歌是家在农村的城市人。诗歌现在踩着的这片南国土地,没有他的家。他不是这个地方的人。而他的户口所在地,离他的老家不远的那个不大不小的城市,也没有他的一草一木,更没有他的一砖一瓦。他在那个城市只有户口本上那张写着他名字轻飘飘的纸。
他户口所在的那个城市,诗歌在那里只上了三年高中。可他来这个位于南国的城市超过了十年,十七岁时来的,今年他二十八,来了十一年。诗歌想都没有想过再回他户口所在的城市,因为他在那里没有片瓦一砖。更不想返回到那片生他养他的老家,虽然那里有他的爹妈,爹妈是亲,可让他住窑洞喝窖水过农村日子太难受。
地处黄土高坡的老家虽说地名叫“响水泉”可老天爷看不上这里,多少年来一直缺水,家乡喝的是逢下雨下雪盆接锹铲回水窖里的雨水雪水,家乡的人比论哪家富裕,不说谁家钱多少,首先是比谁家的水窖大,存水多。
现在他心眼里埋怨起了父亲:要不是父亲十几年前,给他和妹妹每人花了一千元买了两个城市户口,他现在也还是农村人,就有资格理直气壮地参加这次诗歌大奖赛了。
哎,从小就爱写诗爱唱歌的诗歌,现在连参加诗歌大奖赛的资格都没有了,哎声叹气一屁股坐在了树阴下圈着树根的水泥砖上。
菜花儿黄了,
风吹到山那边去了。
这两天把你想死了,
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
黄河里水干了,
河里的鱼娃晾了。
没了水的鱼娃儿活不成了,
心里的疙瘩结下了。
虽说诗歌心里唱的是“花儿”,可歌词一点都不甜美,苦的还像黄连。
“嘿,我说大诗人,大白天的你不去做你的事,在这里发什么呆。”
心里正唱着“花儿”的诗歌,让卖完报纸美莲嫂的巴掌拍得一激灵站了起来,没心没肺的美莲嫂用报纸在抽打诗歌的屁股,把刚才诗歌坐地上沾身的土拍打掉。
大天白日,诗歌不好意思美莲嫂这般亲昵,从美莲嫂手里又把那几张报纸拿了过来,说:“不脏的,我自己来。”美莲嫂关切地看了看他灰灰的愁苦的脸,问他“怎么了,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不会是生病了吧?有病可是要看,别让病影响了参加诗歌大赛”
不说参加诗歌大赛还好,一提,反激起了诗歌的无名火,冲美莲嫂没好气地说:“参加个鬼哟,我根本就没资格参加!”
美莲嫂着急地问诗歌,“你怎么不够资格,你不是外来打工的?”
诗歌抖擞着报纸,指着报纸上那像人得了红眼病红洇洇烂眼圈般的套红边框中印着铅字的消息愤愤说:“这上面要求参加诗歌大赛必须是农村户口,我是城市户口,没资格啊。”
美莲嫂明白了诗歌气极败坏,明知不会错,还是似信非信接过报纸看了看,也目瞪口呆了。好一会,美莲嫂怜爱地瞟了瞟垂头丧气的诗歌,安慰诗歌说:“回去吧,我给你煲汤吃,猪手云豆汤。”
两句温暖的话让诗歌脸色稍稍活泛了些,心知世上的有些事是可遇不可求的,怨天恨地没用,心里自己给自己宽心“天生我才必有用,只因未到有用时。”故作轻松的诗歌拿手里报纸把自己的屁股和裤脚前后上下左右打了打,嘴里酸酸地哼上了家乡的“信天游”
远看你袭人近看你亲,
人好心好爱死个人。
亮红晌午心里明,
全村挑准你一个人。
豌豆豆开花一盏盏灯,
哥哥看你比谁也亲。
三九天长起一亩鲜白菜,
你才是哥哥心中的爱。
和诗歌并肩走着旁边的美莲嫂“扑哧”笑了,你快别酸了,酸得我都要那个了……,诗歌见美莲嫂这刻儿脸更红了。不光脸红了,眼里也泛出了暧昧的水波,水波荡浪让诗歌也有了感觉,几年来都是这样,诗歌凡是遇到烦心事,他就到美莲嫂身上寻找安慰,这也是他在这个洒满阳光的城市,明知立足无望,也不愿回老家去的真实原因。没有了美莲嫂,日子不知会苦成个是什么样子。
诗歌用手臂碰了碰美莲嫂肉几几的胳膊,张口又来了句更酸的;
“青线线那个兰线线蓝格英英的彩,
好一个蓝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
见美莲嫂笑的身上的凹凸花枝般乱颤,颤的诗歌坏坏的给美莲嫂说:“不去菜市场了,你打车回家,我走近路回去。”
美莲嫂看了看诗歌有内容的眼睛,红润秀气的脸宠这会儿又添了层红云,像紫色的葡萄。美莲嫂没吭声,身边有辆出租车驶过,美莲嫂招手上了车。
二、
诗歌其实不叫“诗歌”,叫“石可”。母亲生下他,让父亲给起个名字,为起他的名字把父亲憋了好几天。
他出生那年,年景不好。“响水泉”的家乡地名枉叫了,生他那会儿,老家“响水泉”又七十多天没下一滴雨。诗歌父亲看着快要干涸了的水窖,给他起了个单名“渴”,加上姓叫“石渴”。石渴后来上学到了初中时,认识了几个字的石渴嫌“渴”难听,从打小就爱唱歌编歌的他,知道有个大作曲家叫马可,“南呀么南泥湾,陕北的好江南”就是他作的曲,觉得这个“可”比他的那个“渴”洋气,自作主张地把他的石渴改成了“石可”。
从老家来到这几乎天天晴天,又差不多天天下雨南粤的雷州半岛,雷州半岛特区这里城市的空气比老家湿润多了,空气吸进肺里像吸进了水般的滋润,每天都在给身体中每粒细胞洗澡。
特区这地方人说话像外国话吱吱喳喳的搞不清。发音不准还嘀哩嘟噜像这里的天空,刚才还响晴白日的,一转眼,不知从哪里飞过来几片云彩,接着天上震天动地打几声响雷,马上就滴起了雨滴,不是下起来没个完,要不就还没把地皮撩湿,又滴答完了,抽疯一样一天总要来这么几次,老天爷的脸比三岁小孩子的脸变得还快。
这里人说话难懂,也比老家好,哪像老家,下个雨比女人生个娃娃还难。
天气无常,人们说的话没准调。这边特区的人把他石可叫成了“诗歌”,石可觉得“诗歌”名字更洋气,索性不更正了,诗歌就诗歌,再说哪个作家和诗人没有几个笔名。我这笔名既是文学艺术形式又是名字,一兼二,更美。
诗歌在家乡“响水泉”读完小学,本来按母亲的意思继续在县城读初中、高中。不知诗歌父亲从哪里得知,临近他们省他们县的另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那个产煤炭的城市,可以给农村人下户口,让农村人户口转成城市户口。条件是,落一个人城市户口要给政府交一千块钱,叫什么城市增容费。诗歌父亲听了这个消息,和母亲嘀嘀咕咕了好几晚,想要把诗歌和妹妹的户口落在城市。让炕圪落偷听父母亲说话的诗歌高兴的心怦怦跳。他早想着成为城市人,走油马路,进楼房里上学了。
父亲和母亲合计到钱,父亲刚刚的情绪激昂变得窝囊了,家里拿不出两千块钱。家里最值钱的是二十几只山羊。能卖的只十几只,不能把产羊羔的母羊和没长大的小羊也卖了。
十几年前,羊没有现在值钱,那会儿每斤羊肉才三块多钱,哪像现在猪肉都十几块了。
十几只羊顶多能卖千、八百,剩下那一千块从哪里去找呢?诗歌父亲望着糊了层报纸圆圆的窖洞顶犯开了愁。
第二天,父亲羊不放了,吼诗歌母亲替他放羊。父亲背着三弦和二胡,骑自行车捎着瘦筋筋的诗歌奔了县城。
进了县城边时,诗歌父亲停住自行车,诗歌也跟着跳下了自行车,父亲把他领到一个背静旮旯,有生以来父亲头一次与他郑重的说:“渴娃,今年你十三了,大大(西北土话:爸爸)像你这么大时早开始放羊了。渴娃你说,你长大了是像大大这样一辈子放羊呢?还是有点出息成为城市人?不要说考上大学进北京了。大大现在就想问你,想不想在城市有个好工作?”
懂事的诗歌点了点头。
“那好,大大今天就给你开始实现俄娃娃当城市人理想,大大,今天领你来县城是让你和大大在县城卖唱,大大装瞎子,你给大大也装个残缺人,装胳膊断了的残废人,只有俄们装扮的可怜了,才能换来人的同情,俄们才能唱回钱来。”
诗歌不解地看看黑黑瘦瘦的父亲,问:“我胳膊好好的,咋能装扮成断胳膊?”
白亮亮的阳光晃的父亲眼睛眯缝着虚虚地看着远处说:“这好办,大大给你把胳膊卸了,不过,你可是要忍住点疼,疼过一会就好了,俄们回来时大大再给你把胳膊安上。”
看诗歌迟疑,父亲红着眼睛说:“大大实在是想不出挣钱的办法,只能让俄娃娃跟大大受大苦了。”
看着父亲扑簌簌直往焦渴的地上掉的泪蛋蛋,十三岁的诗歌心里生出一种为父亲解忧愁的男子汉豪情,挺了挺平的像窗玻璃般的胸脯,努着喉嗓把正在变声小公鸡般的尖嗓门往粗里吼,给父亲说:“大大,你卸胳膊吧,俄不怕疼。”
父亲先给诗歌换了身他前几年穿过的衣服,换上衣服的诗歌,打量着露肚脐眼,裤子吊“二羊棒”膝盖的打扮不干了,对父亲说:“大大,这难看死了,不要换了吧?”父亲说:“渴娃,你就依大大一回,俄们不挣多钱,就只挣一千块,挣够了这一千块,加上咱卖羊的钱,你和你妹妹落城里户口的钱就够了。”
“那让同学看见不是羞死了!”诗歌不情愿地说。
“县城离咱‘响水泉’六十来里,你的那些同学有几个能来了县城?再说了,大大一会还要给你化化妆,只要你不说话,别人咋能认出你来?”
父亲说的有道理,诗歌不死声了。
接着,诗歌父亲又教了他几招胳膊断了装可怜的窍门。
诗歌心底永远记着父亲那天给他说的话:“渴娃,你忍着些,大大,只是给你把胳膊的环环卸下来,等后晌,大大再给你装上。挣上了钱,大大领你去吃‘肯德鸡’。”
说着,说着,父亲摩挲着诗歌胳膊的手,猛一下攥紧了,只听父亲低沉地哼了一声,随着不大的一声“咔吧”,诗歌的胳膊从肘弯折了,折的前小臂和大臂皮肉连着,骨头分了家。小胳膊能往前甩,朝后也可以晃,和大臂折叠在一起了。巨大的疼痛让诗歌抱着胳臂“哇哇”哭起来,诗歌的哭喊让父亲心疼的脸煞白,泪下来了,汗也下来了,对诗歌说:“渴娃,好娃娃,忍着些,相信大大能给你把胳膊弄得脱了臼,也能给你安上,渴娃听话,不哭,疼过这一会就好了。”
疼的钻心的诗歌知道父亲有接骨头的本事,平常日子,家里的羊有哪只摔断了腿,父亲就给羊儿们捏咕捏咕,先还走路一栽一栽的那些羊儿们,经过父亲一阵捏咕,不大一会,羊儿就又活蹦乱跳了。
想起父亲的这些本事,诗歌觉得疼痛轻了。
“让俄渴娃受苦了,让俄渴娃饥荒了。”父亲唠唠着慌慌的没头没脸给诗歌瘦的像筷子头的脸蛋上抹了几把细面面土。然后,他也换了身破烂衣裳,把二十块钱买的旧自行车锁在一家人家的墙脚边。两只手一手捏着上眼皮,一手捏着下眼皮,不知怎么着只翻了翻上下眼皮,顿时父亲眼球看不见了,只能从眼睛忽闪的一条火柴棍宽缝隙里看见丝白眼仁,父亲竟日能的把黑眼球转在了眼球后面。
一眨眼父亲变成了瞎子,比赵本山装扮的瞎子还像。父亲活灵活现的变化,让诗歌胳膊的疼痛轻了些,咧嘴苦笑了。
父亲腰里系了根绳子,让诗歌牵着,把背着的二胡从后背上取下,手腕一抖,马上凄婉的“二泉映月”便从父亲边走边拉的二胡里飞了出来,在一群和诗歌差不多大的半大小子们哄闹和簇拥下,诗歌把父亲牵到县城百货大楼前,也许父亲从白眼仁里看见了百货大楼,一张口,凄凉的新词唱旧调“走西口”便“咯嘣嘣”地蹦出了父亲嘴巴;
叫一声妹妹哟噢泪花花要流,
泪蛋蛋就是哥哥心上的油。
实心心的哥哥,哥哥哎嗨不呀不想走,
真魂魂嗨来嗨绕妹妹你呀么身呀么身左右。
叫声妹妹你莫要哭,
哭成个泪人人你叫哥哥咋上路?
人常说树挪死来哎嗨人呀人呀挪活,
又不是哥来哥哥我一人呀么走呀么走西口。
啊,亲亲!啊,亲亲!
我挣上它十斗八斗就要么往回走。
叫声妹妹你莫犯呀愁,
愁煞了亲亲,哥哥我心上不好活。
为你码好柴来哎嗨为你换回油,
枣树那圪针为你插了一墙头。
哎,亲亲!哎,亲亲!
你到夜晚守住大门放呀么放开狗。
叫一声妹妹哟泪莫流,
挣上它十斗八斗我就往回哟走。
仰天高歌的父亲唱着唱着,真真从黑眼珠不知翻到哪里了的眼里滴出了“哗哗”的泪水,不知是父亲的难为还是胳膊这会儿的火烧火燎,右手拿着讨钱的塑料盆,手臂还托着滴溜打转左手的诗歌也想要哭,怕父亲看着伤心,他让眼皮努力挟着眼泪不让泪水滴出眼睛,费劲的在眼里汪汪着。
诗歌那黑黑的眼球里荡漾着盈盈的泪水,红紫的肿的像面前女人手提溜的小枕头般粗面包的胳膊,让围看着诗歌的女人和其他的人不忍。
这个穿薄如蝉翼云彩一样轻飘白裙子的女人,盯着诗歌让汗水把小脸上的土冲得一道道的灰头灰脸,眼圈红了,忽搧忽搧的毛眼眼里泛出了水波,低头从手腕挂的精巧手提包里拿出了十块钱,看了看,手又返回了包包……
诗歌心直抖,恨不得上去把女人伸回包里白腻腻的手拽住,无奈他左手“残了”,右手托着残手,还拿着讨钱的塑料盆,再没长第三只手。
白白净净的女人伸回包里的手,又拿了出来,手里握着不是一张十块的钱了,变成了两张,两张像燕子一样黑灰颜色的十块钱,像两只喜燕飞进了诗歌手里端着的红红塑料盆。
父亲肯定是瞅到了那两只飞来的“燕子”,高亢的“走西口”把人唱得更心碎了。
跟了忽悠的会哄哄,随了会唱的能哼哼。被父亲调教的打小小就爱唱“走西口”的诗歌,曾年年在学校争得歌咏大赛第一名的诗歌,把刚才飞进盆里的两只“燕子”拿出来转放回脖子上挂着的书包里的诗歌,不怕见着熟人了,头一仰止住往外要喷的泪水,也张口唱开了“信天游”
去年,我从马背上摔下来,
手没摔断腿也在。
今年,我从妈妈眼里被甩开,
心啊,已饥荒成一片又一片。
地上的马儿呀一溜溜的烟,
天上的鹞子呀扑楞楞地转。
渴娃我要学马儿朝前跑呀,
不学那鹞子就地划圈圈。
诗歌一唱,吼喊着过来要轰他们父子离开的两个保安,停止了脚步,闭了声,你看看我,我眊眊你,往盆里放了两块钱走了,两片浅绿色的一块钱票子,像两片绿叶,引来了更多的“喜燕”,甚至还有一张粉红色的百元票子,像一只彩色的大蝴蝶在五颜六色的盆子里翻飞。
三、
傍晚回家前,诗歌父亲在路途上就把诗歌胳膊归了位,可进了家门诗歌胳膊还是肿得发亮,母亲瞅见诗歌用布条拴了块木板吊着的手臂,脸立时变得纸一样白,急着问诗歌,“咋了,渴娃你把胳膊怎么着了?”诗歌委曲地抬头看了看父亲,没说话。
母亲扑到父亲面前,愤怒地质问父亲,父亲故作轻松地把缘由给母亲说了,没等父亲把话说完,母亲像愤怒的山羊打架,一头撞在父亲的胸脯上,母亲披头散发边骂边哭边抓,把脸上添了几道血痕的父亲从炕头打到了地下打出了屋外,直到父亲在外面一个劲地向母亲央求再也不办这种蠢事了,脸上挂着泪的母亲,这才气咻咻地给父亲开了门。
晚上,父亲讨好地替母亲烧了一大锅水,让母亲用热毛巾给诗歌的胳膊敷了又敷。累了一天的诗歌躺在炕上迷糊中听父亲对母亲说:“明天,俄带咱渴娃去给下户口的那个市再去唱,那里的人比咱这里有钱,俄们要在那里住一晚。”
母亲没吭声,气乎乎地把父亲赶到放粮食的凉窑去睡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把诗歌叫了起来,说:“渴娃,咱趁天气凉快赶紧走。”出了窑,父亲叫诗歌稍等等,从睡窑里提了个暖壶急匆匆又折回了昨晚睡的凉窑。母亲声唤诗歌:“把锅台上放的十来个煮鸡蛋拿上,再提溜两个腌‘蔓净’疙蛋就鸡蛋吃。”
睡窑出门,父亲已推车站在当院等诗歌了。母亲不放心地起身在院门口送他们父子,父亲上自行车时诗歌感觉父亲腿不得劲,没多想,向母亲扬了扬手,跳上父亲骑的自行车,一溜大下坡轻快地扎进了黎明前的黑暗。
等父亲带着诗歌骑了二百来里地自行车,进了挨着“响水泉”那个不属于他们省的城市,后晌了。父亲和诗歌花了十块钱买了两张门票进了人民公园,他们的自行车不让进,父亲花了一块钱把车子在公园门口存起。诗歌发现父亲的腿走起路来吃劲,一拐一拐的好难看,知道是父亲骑车骑的腿累了,懂事的把父亲背的二胡和三弦替父亲背了,生平头一次幸福地与父亲走进了公园。
见里面有厕所,父亲让诗歌站立等等,说:“俄去下厕所。”父亲回来时,诗歌哭了,父亲在厕所换了条把长裤铰了半截子将就穿的短裤,裸露在外面的两条腿,一条好好的,长满了青筋和汗毛,另一条腿却布满了胡豆大数不清的水泡,还有好几个大水泡让裤子磨破了,皮开肉绽血淋糊啦的让诗歌不敢看。
诗歌吃惊的一个劲嚷嚷:“大大,你的腿怎么了,怎么烂成了这样。”诗歌父亲疲惫的脸灰灰的说:“渴娃别喊,快把外面的衣服脱了。俄们继续演戏。”
见诗歌急的眼泪滚了出来,诗歌父亲埋怨自己说:“大大,不小心把暖壶掉地上打碎了,滚开水泼腿上了。”诗歌不相信:“大夏天的,大大你用开水干什么呀。”诗歌父亲苦笑了一下说:“娃娃家少操那么多心,俄带着“獾子油”呢,明天俄们回去时,大大把“獾子油”抹腿上,一搽就好了,没事的。”
(獾子,是诗歌老家野地一种和狐狸差不多大的小动物,用它熬出的油是一种特效的治疗烧烫伤的药。)
听父亲说明天才抹“獾子油”,诗歌明白了,父亲今天是接着再编苦肉计,把昨天诗歌的受疼痛换成了他自己。父亲自编的苦肉计给诗歌弱小的心口上压了盘石磨,沉甸甸压的让他喘不过气。
公园里人多,上年纪的人也多,老年人都喜欢听诗歌父亲拉出的悠扬凄美的《梁祝》、《牧歌》二胡曲。
当父子二人一个苍劲一个稚嫩联唱起一个接一个的“走西口”,再看看这吊着胳膊,跛着腿的一老一少,望着诗歌父亲血迹斑斑的伤腿,让好几个老头老太太流出了眼泪,纷纷把身上的零钱兜底掏了出来。
这天是星期六,公园里围观诗歌父子的人越来越多,父亲给诗歌说:“渴娃,你给咱可劲唱。大大腿疼的站不住了,坐地上给你拉胡胡。”
十三岁的诗歌是从这天长大的,他偷偷瞧着父亲用滚烫的开水烫出的像长满了烂葡萄腿,望了一望刺眼的大太阳发誓要替父亲多挣钱。
那天从诗歌嘴里滚出的“信天游”、“花儿”、还有“走西口”,就像来的路上父亲指给他看似从天上下来的黄河水,诗歌的歌声不是从嘴里唱出来,是伴着父亲的血泪和他胳膊的疼痛从心尖里淌出来的。
第二天,诗歌父子又来了公园。前一晚,父子俩歪斜在火车站的长椅上,诗歌父亲腿疼的躺在椅子上睡不着反过来折过去,诗歌劝父亲把獾子油抹上,父亲说:“再坚持一天,明天唱完再抹,今晚抹上了,腿好了,城里人就不可怜咱了。”疼的没法子一个劲“丝丝”直吸气的父亲,到候车室洗脸的地方,用水管子里的水往伤腿上浇了一遍又一遍。
半夜时,歪在父亲怀里的诗歌听一个男人高声大嗓地让他们父子起来,诗歌不高兴地揉了揉朦胧不清的眼,见面前站着个面色冷峻的警察,要看父亲的身份证,父亲陪着笑脸谦卑地巴结警察说:“俄们是从‘响水泉’过来的,俄们那里还没有给农村办开身份证。”
“身份证都办开几年了,你怎么会没有身份证?”
“俄也不知道,俄们那个庄上的人都没有身份证,公家人说要把身份证照片送到省里印,慢的很。”父亲陪着笑脸说,诗歌看这会儿“丝丝”直吸气的父亲笑脸比哭还难看。
诗歌心想“身份证是你们警察给办的,是你们办不上,咋能怨俄大大没有身份证?”
警察也许听父亲说的在理,不再和父亲叮对身份证,拿起父亲身边的二胡掂了掂,明知故问问父亲:“你会拉二胡?”
诗歌翻眼瞅警察,心想“查身份证就查身份证,管球俄们会不会拉二胡。
见诗歌父亲点头,警察让父亲拉一拉听听,父亲操起二胡就拉,诗歌在一旁直呕父亲的气,警察又不给钱,让你拉就拉,看把你吓成个甚。
面前这个警察爱听二胡,听诗歌父亲把“二泉映月”拉得婉婉转转,又听父亲说他和诗歌来市里是来卖唱挣钱的,好为了买市里的城里人户口,警察看了看父亲流着黄水的伤腿,叹了口气给了父亲十块钱走了。
市里卖唱两天挣的钱,加上诗歌父子在县城的收入,父亲边点钱边兴奋地说,“不唱了,走,大大领你去吃‘肯德鸡’。”
听父亲这样说,诗歌兴奋地问父亲:“大大,钱挣够了?”
父亲说:“不够也差不多了。”
不过,诗歌有生以来的这第一次挣钱,让他没有吃上“肯德鸡”,父亲在“肯德鸡”店要给他买“肯德鸡”,诗歌不让,只让父亲花五块钱给他买了个“汉堡包”。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吃“汉堡包”,也是他终生最后一次吃“汉堡包”,他发誓此生再不吃“汉堡包”了。
咋了?原来,诗歌和父亲来市里第二天半后晌那会儿把卖唱收了摊,父亲让诗歌在树阴下等一会,他去去就来,然后,匆匆骑自行车走了。功夫不大父亲回来,脸色灰黄的像刚从羊身上剥下来的烂羊皮。父亲给钱让诗歌买两只雪糕,说:“心搧的慌。”然后,无力地躺进了树阴凉,父子俩一人一支雪糕吃完,父亲脸色好了些。兴奋地说:“走,大大领你去吃‘肯德鸡’。”
诗歌父亲在“肯德鸡”店抖抖颤颤从衣兜掏钱买“汉堡包”时,兜里掉出了一张纸片,父亲没注意,急急地拐七扭八的到柜台给诗歌买“汉堡包”,见父亲掉了东西,诗歌替父亲捡了,看纸片是血液中心站开的,上面记着抽血400cc付营养费200元。
小小的诗歌一下子明白了,刚才父亲为什么脸色那么苍白,原来父亲到血站卖血去了。见父亲端着“汉堡包”过来了,诗歌哀怨地把和父亲脸色一样寡白的纸片团了团,踩在了脚底。
见诗歌一口、一口努力地把不是滋味的,用父亲的伤,父亲的血换来的‘汉堡包’往肚里塞。看诗歌吃的费力,父亲心疼地说:“看把俄儿饥荒的,‘汉堡包’是不是和咱家的馍一样咽人,大大给你再买杯可口可乐,顺顺嘴。”
从此以后,诗歌看见虚肿松包的“汉堡包”,眼面前就浮现出父亲流着脓水布满了潦泡烫的难看的腿,觉得“汉堡包”里搀和有父亲的鲜血,让他不敢张口。
四、
辛酸的往事,想一想就算了,老想,不光心里灰灰的,还啥事情都没心思干,这会儿诗歌只想把他的脸埋进美莲嫂的怀里,让她那两只玉兰花般洁白硕大的乳房挤压他的脸颊。
两人登上快乐的巅峰好大一会,美莲嫂推了推诗歌,柔声说:“好了,好了,阿玉要回来了,我要给她烧饭去了。”
阿玉是美莲嫂的女儿,今年十岁了,诗歌抬腕看了看表,是该到不得不停止的时辰了,不甘心地从欲望的山尖滚落下来。
美莲嫂下床把衣裤穿好,用梳子把刚才搞乱了的头发拢了拢,和诗歌说:“我想过了,你虽说是城市户口,可是你来南方都十几年了,早已不是那里的人。再说,你户口从农村迁到了城市,也可以再从城里迁回农村啊。”
美莲嫂提醒了诗歌,是啊,当初父亲花了两千块钱给他和妹妹办得城市户口,如今城市户口变成了鸡肋,成了无肉,扔了又可惜的干骨头。要这个徒有虚名的城市户口有何用!我从城市把户口再迁回“响水泉”,不就又成了农村人了。
没球本事还尽往复杂地方想,诗歌不禁自己埋怨开了自己。
想到哪,做到哪,诗歌马上就要给“响水泉”三娃家里打电话,让他转告父亲把他的户口从城里再迁回“响水泉”。
见诗歌要给老家打电话,美莲嫂阻止说:“你着急啥,晚上我问问大老林,看这么着办成不成?问好了手续怎么办?再说嘛。”
听美莲嫂晚上要叫大老林,诗歌心里醋海直翻,大老林是美莲嫂的情人,是管他们这个管段的警察,听美莲嫂说:“和她好了有几年了。”
美莲嫂见诗歌脸沉了,暧和的问诗歌:“怎么了,吃醋了?吃醋你娶我呀,你娶了我,别说去你们那个喝水都喝不上的‘响水泉’,到天边我都跟你走。”
几句话,把诗歌问住了,真娶美莲嫂他没有勇气,虽说,家里早在催着他结婚生子,他也一直在电话里给父母说有女朋友在谈。可真让他把大他好几岁又带着孩子阿玉的美莲嫂娶回老家,那不是要活生生的气死父母亲。
见诗歌尴尬的讪笑,美莲嫂拧了拧他的脸蛋,说:“大诗人,别再瞎想了,这会儿,你是要赶紧着写你的诗歌,特区农民工没有几百万,几十万肯定有,你能保证你一定能获奖?”说完,清风一般出了门。
说起来,美莲嫂也是农村人,十几年前,市里把她家的房屋,承包的土地,统统开发搞成了开发区,政府给她和老公家在开发区边上盖了房子,又给了她们几十万块的补偿金,还让美莲嫂和老公也成了开发区工厂里的工人。
美莲嫂的老公一天也没有到工厂上班,嫌上班让人管着不自由,把公家补偿的钱拿出来在家门口开了个小超市,自己当老板做起了买卖。
开发区里有几万的打工者,小超市开在四通八达的路边,人流整天熙熙攘攘的川流不息,小超市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小超市里那些不起眼的食品、日用品几天就卖完要再进次货。随着生意的红火,美莲嫂老公的心跟着花了,和他雇用的几个外来妹打得火热。像一只贪嘴的猫,把盘子里的鲜鱼都尝了尝后,选了一条最鲜美的—在雇用的几个外来妹里,把选中的那个长得最好看的外来妹搂进了怀。
美莲嫂老公怕其她的外来妹不依他,也怕美莲嫂和他闹,把花花事情做的神鬼不知。悄悄地先让他的姐姐代管起了超市,别让那几个他动过的外来妹找到他。又在外面买了一处房,和他选中的那个外来妹过起了包二奶生活。
等整天早出晚归的美莲嫂知道老公跑了,一切都变了,连小超市里的外来妹也全换了,原先的几个外来妹;愿吃哑吧亏的,含着泪默默地让老板炒了“鱿鱼”。性子烈不甘心吃哑吧亏的也只能认了打发的那几个钱,怏怏地走了。再不走,新来的女老板会找几个烂崽威胁加殴辱。当初是自己心甘情愿贴老板,这会儿孤零零一个外地人,也只有哑巴吃黄连退避三舍了。
这些年港澳那边的,内地来这里挣了钱的,好些人在开发区买了房子,包了二奶。包二奶的大多不把家里原配老婆离了,只是在外面家外有家。他们认为把家里原配老婆离了,会给他们的生意带来晦气,渐渐地,美莲嫂她们这地方包二奶成了气候。再说开发区里那些成千上万的打工妹,又有几个不想在这里有个家。
于是,特区这里原先世代耕田种地的男人们,变了,变得一个个像诗歌他们“响水泉”红衣裳绿尾巴的土公鸡,虽然被烟酒浸淫的喉嗓打起鸣来嘶哑的难听,可土公鸡的羽毛依旧光彩眩目。
屋漏偏逢连阴雨,老公包了二奶,美莲嫂打工的工厂跟着也倒闭了。美莲嫂打工的工厂那个香港老板是假的。假老板到大陆这边来,钞票加美女公关把开发区的几个政府官员拉下了水,骗了国内银行几个亿的资金跑了,老板跑了也让打工没几年的美莲嫂下了岗。
后来,多亏管段警察大老林给美莲嫂搞了个下岗工嫂报刊亭,才让美莲嫂不坐吃山空生活有了着落。
大老林的老婆瘫痪有几年了,美莲嫂在卖报纸时“近水楼台先得月”证实了大老林老婆瘫痪在床:《南粤特区报》评十佳美好家庭,把大老林评上了。说他十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家务重,工作忙,再给瘫痪在床老婆端屎端尿也没有请过假,更没有耽误过工作。
大老林在开发区这块当管段民警有十多年了。
美莲嫂知道大老林日子过的寂寞。
大老林给美莲嫂和女儿又找了只饭碗,美莲嫂没有什么报答的,就经常的给大老林烧些菜,让他给瘫痪的老婆带回去,还经常去大老林家帮大老林洗洗被子,收拾下屋子,让大老林少做些家务事松口气。
一来二去,大老林和美莲嫂有了私情,美莲嫂不计较大老林不和老婆离婚,就是大老林想和老婆离婚,美莲嫂也不会让大老林离,让大老林抛下老婆和她过日子,那会把大老林老婆推向绝望,会遭报应的。美莲嫂只是尽可能用女人火热的胸脯熨平大老林让生活不幸挤压的愁眉不展的眉头。
这些,都是美莲嫂情热时给诗歌讲的,大老林不光帮助过美莲嫂,没有大老林,诗歌在特区也站不住脚。这还要从诗歌刚来特区时说起……
诗歌父子那年靠卖唱,加上父亲偷偷卖血,再加上卖了十几只育肥的羊,终于给诗歌和妹妹两人买上了城市户口。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