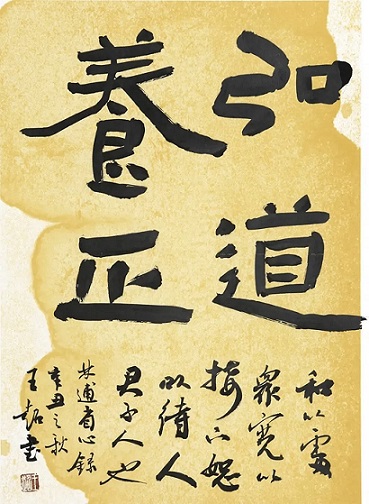堂弟在外地经营着一家厂子,干的红红火火,挣了不少钱。每年春节,他总是带着几条软中华回来过年,并邀我去他家吃顿饭,喝上二两他带来的拴红绳小白瓶。两人晕乎乎地说些过年的话,不轻不重的,一晃就这样过去了十多个年头。
前几天,堂弟打电话叫我去他公司聚聚,我便欣然前往。
坐在他办公室的茶桌前,却迟迟不见人影。正纳闷时,他似笑非笑地出现在眼前。“哥,我去买烟了,跑了好几家店才买到你常抽的白将。”我带着点不耐烦,悄悄瞥了堂弟一眼——只见他头发蓬松,面色如霜打的秋叶,失去了往日的红润,眼神里透出深深的疲惫与无助。一身青色外套皱皱巴巴,脖子上的领带拧成了圈,与他灰暗的脸形成一副极不协调的画面。
“怎么想起叫我来了?”“哥,今年真是难熬,想和你聊聊。知道你爱抽白将军,特地去买了两盒。”他把烟放到我面前,又泡上一壶浓茶,话匣子便打开了。
“哥,这几年知道你从村长位置退下来,怕耽误你清静,一直没敢打扰。如今账款难收,眼看就要过年,一大堆事等着处理,愁得吃不下、睡不着,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不,想起你来了,就想请你来说说话。”我沉默片刻,直言道:“几年前我就跟你说过,企业产品要有自己的技术核心,要申请专利、做品牌,改造传统工艺,摆脱家族式管理,往高质量走。你总做代加工、跟在别人后面挣钱,不是长久之计。你当时总是哈哈应付,现在知道厉害了吧?”堂弟面红耳赤,嘴唇微抖,声音发急:“哥,那几年活儿多、生意太好,你说的那些核心、品牌,我根本没往心里去……”话音落下,我俩都陷入沉默,室内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
出于习惯,我顺手掏出口袋的烟,点一根却被堂弟猛地拦下:“哥,我知道你一抽烟就要开始训我了。先别抽,快给我出出主意,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时暮色已沉,窗外稀疏的星光透进来,与室内昏黄的灯光交织在一起,仿佛悄悄映照着我俩凝重的神色。
“你现在给大企业供货,量大、投入多,回款又慢。保工资、保税收、保运转是头等大事。长此以往,资金链难免断裂,负债过重的话,银行也可能不再续贷,厂子运转肯定会受影响。”“是啊,我就是愁这个。要想解套,往后该怎么走?”看着堂弟焦虑的神情,我深深叹了口气:“眼下最要紧的是讨回欠款。为了厂子能活下去,为了工人能拿到工资,该找法律途径就得找。”“哥,不行啊,万一起诉闹翻了,以后人家不给定单了怎么办?”
我说:“把烟拿过来,我抽两口想想。”堂弟只好把那根被他捏得皱皱巴巴的白将递给我。“以前你回家过年,带的都是软中华,还显摆说,‘哥,这是3字头的,托人买的’。今天怎么买白将了?”堂弟的脸一下子像挨了巴掌似的,红一阵白一阵。“你这人就是死要面子硬撑,从小就这样,没少挨叔的骂。”他垂下了头。
这时弟媳推门进来,寒暄两句,说了一句实在话:“哥,你兄弟怕得罪客户,断了后路。可眼下要是关门停工,工人散了,以后有单子也赶不出来。还不如先顾好眼前,走一步看一步。我觉得你说得在理。”正说着,前年弟媳带回老家的那只花猫,“喵喵”地慢悠悠走进来。我仔细一看,从前圆润发亮、眼睛炯炯有神的它,如今走路拖沓,毛发像粘在一起的毡片,眼角还挂着粘稠的泪痕,像个刚哭过的孩子。
堂弟似乎察觉到我目光中的叹息,更加局促起来。他抓过白将军,一根接一根地闷头抽着,不一会儿,一包烟就被我俩抽完了。
办公室里早已烟雾缭绕。窗外透进的光,像被纱幔滤过似的,朦胧地漫进屋内,缠绕在各个角落。排风扇开着,却被浓烟堵得发出“哼唧哼唧”的闷响。弟媳连忙推开窗户,清风涌入的刹那,堂弟缓缓直起身子:“哥,就这么办吧。明天我就把法律顾问请来。”
弟媳炒了两个小菜,拿来一瓶散装白酒,摆在茶桌上。“哥,老规矩,你六两,我四两,等下给你找代驾。”说着,堂弟拆开了另一包白将军。
年,悄悄地近了。堂弟又一次打来电话:“哥,通过法律顾问和对方交涉,第一笔材料款已经打过来了。这办法还真行,厂子有盼头了。”“快过年了,先把工人工资结了,把税缴上。”我提醒他。“好,明天就全部落实。年三十晚上,咱们还是在老家聚。”堂弟应着。我又随口问:“烟还抽软中吗?”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
没多久,堂弟回家,带了两条白将军香烟。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