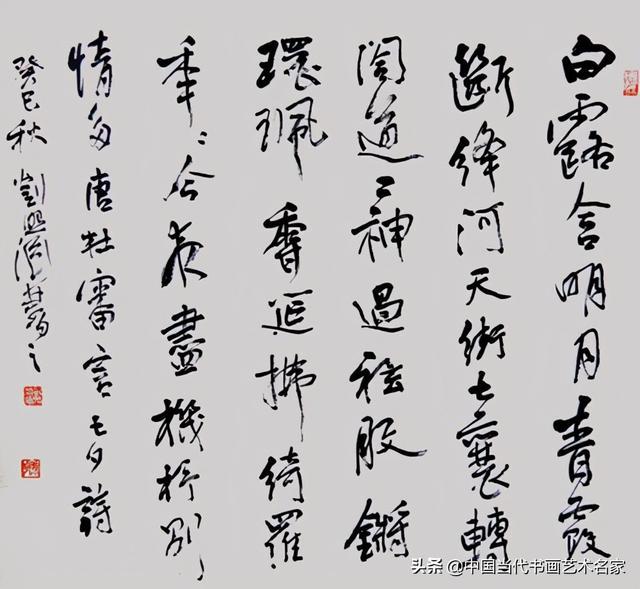题记: 那些在清贫里发芽的星星,曾是童年最奢侈的糖纸,多年后才读懂,穷困的褶皱里藏着最丰盈的月光。 瓦罐煨着稀粥,补丁缀满衣裳,可风掠过山坡松林的声响,至今仍在记忆里叮咚作响,原来贫穷的土壤,也能长出永不褪色的童话。时光筛落金银,独留下褪色的粗布衣裳、结霜的屋檐与母亲眼角的笑纹,原来贫瘠岁月里,藏着最富有的童年。
1
1959年至1961年期间,我国发生的全国性严重经济困难。这段时期因连续自然灾害叠加“大跃进”运动等政策失误,导致粮食生产受挫,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最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史称“三年困难时期”。
我出在三年困难时期中最困难的1960年农历九月。9月虽然是金黄的粮食收获季节,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吃食堂”制,全生产队近200人在一口锅里吃饭,家家户户不准私自开伙,那怕在家里熬一碗粥条件都不具备。生产队刚收的新粮,要交够公粮、留足储备粮,剩下的粮食要精打细算,吃到第二年夏粮收回来时。队长的口头禅“你们是想有粮一顿怂,无粮敲匾桶(装粮的家具)”食堂仍然是一日两餐,以搭配了季节蔬菜,如洋芋、红苕、南瓜、红(白)萝卜……的稀饭为主。听我母亲说,她怀上我以前,到生下我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几乎顿顿都是喝红萝卜稀饭,以至于后来看见红萝卜稀饭就反胃。我出生后全靠母乳,一人的饭都吃不饱,还要喂养我,给我断奶时,生产队的食堂也停办了。
我在母体中和出生后那段时间,先天性的营养不良。我们三兄弟中,两个弟弟比我晚出生6年、9年,那时生活条件也不太好,可已经大有好转。我身高1.7米,比两个弟弟矮了10公分。
听我母亲说过这样一件事,我一直没忘。1961深秋的一天傍晚,我家邻居肖婆婆(是个五保户),在她家火垄坑用个洋瓷缸子煮了一把苦麻菜,见我妈饿得不行,给她挑了一筷子野菜,在夜色下她吃了一口,可怎么也嚼不烂,吐出来在油灯下才发现是一只大猪儿虫,当时恶心的就呕吐不止,把吃下的一口野菜吐干净,最后吐出的全是黄水。原来肖婆婆眼神不好,在野地里把了几窝苦麻菜,担心别人发现了没交给食堂,会被生产队队长批评,择菜、洗菜时,心里紧张,慌慌忙忙没看见菜上的虫,恰好又被我母亲吃到了。
2
那个年代太穷了,感觉啥都稀缺,最缺不过还是“粮食”。我在长身体时,时时感觉人处于一种饥饿状态,走到哪总想找口吃的东西。小时候把我饿很了,直到现在,啥都能吃、吃啥都香、啥都能吃饱,特别爱吃肉。
我家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老四,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在生产队挣工分。母亲负责家务和经管子女。年终生产队决算,我家工分少,年年都是“缺粮户”,母亲能干又会精打细算,可年年农历二三月青黄不接时,仍出现断炊的情况。
那些年自留地里春天栽洋芋、夏末季节押红苕,收获的洋芋搭饭做菜、红苕挖回来后,煮稀饭做蒸饭米用得少,不够的部分红苕填补。锅里很少有剩饭的时候。为了多吃一点饭,我自小养成了吃饭速度过快的坏毛病。我第一碗搯多半碗,第二碗把饭按实,冒冒地搯上一碗,三个姐姐第一碗搯得多,吃得又慢,结果搯第二碗时,锅里没有饭了或只剩下洋芋、红苕了。
为了解决缺少食物的问题,父亲联系了工农饭店,每天给饭店做一座(计量单位,八斤黄豆)豆腐,报酬豆渣归我家。那时没有打浆机,磨豆子全靠手推石磨,推磨的任务就落在了从生产队下工回家的父亲身上。磨一座豆腐的黄豆要用一个多小时,父亲推磨时,我与三个姐姐给搭手。有时父亲有事顾不上,就由我和三个姐姐来完成。大姐推50转、二姐推50转,然后三姐推、我接着推,再来下一轮,直至推完。母亲负责烧水冲浆、过浆、烧浆、点浆水、压豆腐。父亲第二天早早起床,把豆腐给饭店送去,回来后要从小河沟挑一缸水,再到生产队上工。做一座豆腐落下一大盆豆渣,一半早饭做米饭搭饭,有时炒豆渣,放点调料做下饭的菜,另一半喂猪做猪饲料。豆渣不管怎么吃,口感都不好,这么多年了,再也不想吃豆渣了。
有一年春天里,在青黄不接时,家里啥都吃完了断了顿,头天下午都没吃饭,到了第二天中午还是揭不开锅,我们饿得坐在厨房板凳上等母亲做饭。母亲端着盆到邻居家借粮,跑了一圈,好话说尽没借着,看我们饿得话都不想说,她也眼泪汪汪实在没办法。到了下午两点多了,她从木箱里翻出一块银元,那还是她出嫁时我外爷给她的,让我拿到银行去换钱。银行的柜台高,我只比柜台高出头顶。叫了几声阿姨,柜台里的一名女工作人员站起来问我干啥。我把银元递给她说我换钱。她接过银元用拇指与食指指尖夹住,吹一口气,放到耳朵上听响声,然后又在地板上摔了两下,判断银元的真假,在确认了是真银元后,递给了5元钱。母亲有了这5元钱,又找出积攒下的10斤粮票,到县粮站买回了10斤米,给我们做了一锅大米蒸饭吃了。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一点都不假,吃了饭身上有了劲,该干活的干活去了,我又能在外面到处疯玩。
小溪和椒溪河是我获取食物的地方。门前那条小溪,每到夏秋时节螃蟹特别多,到了下午我们拿上脸盆去抓螃蟹,水中搬开一块石头,下面就有几只螃蟹,一会儿工夫就能捉半盆,端回家去掉螃蟹壳和内藏,将其洗干净,在锅里小火慢烘,使其黄脆。没有油只放点盐和调料面,吃在嘴里脆嘣嘣的,用于晚上充饥。
椒溪河里鱼多,我人小不会撒网,钓鱼没技术,我就端簸簸鱼,有时一簸簸能端十几条一小拤长的鱼。我母亲十分支持我,给我找端鱼的竹簸簸、缝制蒙簸的白布、炒制羊油麦麸子。我在河水中找河潭下端一两尺深的地方,安放好竹簸,静等鱼儿贪吃粘在布口上羊油麦麸子而钻入竹簸内。见鱼上得差不多了,我就慢慢轻轻走过去,端起竹簸、倒尽水、取出鱼,继续安放竹簸簸。在等待鱼进竹簸簸时,我用带去的剪刀把鱼剖好洗净,晾晒在石头上。拿回家有干鱼有鲜鱼。到了汛期,椒溪河涨洪水,拿个撮箕站在岸边的回水湾处捞浑水鱼。鱼被泥沙水呛了,用撮箕在河水里往上捞,提起撮箕鱼在里面蹦跶不停,有一次我还捞起一只鳖来。那时家里子女多,父母也从不担心我们会被洪水卷走了。
我家亲戚多,过年互相拜年,要送几包副食,如点心、麻饼、茶果等。收到这些礼品,父母要给我们叮嘱,这些东西都不准谁动,后面要一家一家回礼。我家穷,无钱买这些礼品,收舅舅家给姨姨家送去,收姨姨家给姑姑家送去……那些副食礼品都是用纸包起来用纸绳捆扎,饿得很了,我就不顾父母的叮嘱,今天偷吃一点、明天偷吃一点,到了去给亲戚回礼时,被我偷吃的那一包就无法用了,母亲气得把我们叫来叮对,是谁偷吃了的?为此我挨过打挨过骂。
3
俗话说“有没有吃得看脸上,有没有穿的上看身上”。温饱问题是人生存的基本问题。缺吃的家庭必然缺穿。
我上面是三个姐姐,她们穿小了的衣服我作为一个男娃没法穿,况且她们的衣服不穿烂下不了身。衣服少无啥可换洗,丁在身上穿,那种棉布衣服要不了多长时间就穿烂了。特别像我这种男娃,特别匪,上山下河、爬树掏鸟窝、翻石坎偷果子……衣服的倒拐子、裤子的膝盖、屁股和布鞋的脚指头部位烂得最快,破了烂了要母亲给补、补了又烂、补丁上面摞补丁。
现在拍摄的反映战争题材或困难时期的影视剧,准备服装的工作人员可能都是比较年轻的80后、90后,毫无生活经验,衣服、裤子上打补丁,位置选得不对,不清楚补丁应打什么位置。伟人有张在延安窑洞前给抗大学生做报告的照片,膝盖部位打着矩形的长补丁,真实地反映出那时生活的艰苦。
我上二年级那一年的夏天,母亲给我做的一双布鞋,鞋面是黑色灯草绒布料,刚上脚上就略有点小,只有这样一双鞋,那时时兴玩“跳方”游戏,在地方画出一列五个方格,顶部双方格,脚下放一瓦片,连踢带跳,时间不长,鞋前面先是大脚趾头露出来了,接着又露出另几个脚趾头,鞋又小将就几天就穿不成了。家里穷无钱去给我买鞋,母亲给我做一双布鞋吧,从剪鞋样、糊鞋底、纳鞋底、做鞋帮、上鞋帮,要很长时间。仅糊鞋底就不容易,是用魔芋浆糊一层一层的把旧衣服布累积起来的,要晾晒干才能一针一针纳鞋底。纳一双鞋底就要千针万线。我没鞋穿就打光脚板去上学。下雨天还好说,晴天太阳把路面晒得滚烫,中午放学回家,这近一里多的土石路面,石子割脚不说,把脚底烫得无法下地。我哭着不去上学了,父亲不知在哪借了一点钱给我买了双轮胎底布鞋。我吸取了教训,这双鞋爱惜得很,下雨不穿、玩“跳方”游戏不穿。
家里人多,进入秋天淋雨季,母亲就开始给家人缝棉衣,头年冬天穿过的,全部拆洗,有的加长放大添棉花,有的要做新的,全靠手工缝制,必须保证冬季天冷人人有一件棉袄能穿上身。我记事起好像没穿过棉裤,天冷了里面加一条破烂旧单裤。没有穿过棉鞋,更别说穿袜子了,冷得很时,脚上抱过棕片,年年脚上长冻疮。晚上用热水泡脚,睡到半夜冻疮处奇痒难忍,听说山坡上生长那种形似馒头状的“灰包”能治冻疮,捡拾回家,从中剖开按在冻疮上用布包裹,别说还真有效。
我上初一时,生产大队(村)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大姐是宣传队的骨干。宣传队请袁家庄小学教师张成杰当导演,我常去看他们排节目,张老师有件米色旧夹克衣服太小了,他已穿不成了就送给了我,我穿上有点大,把袖子挽起来也勉强能穿。我稀罕得很,当礼服一样,一直穿到初中毕业,毕业证上的照片就穿的是那件衣服。
衣服少、无法常换常洗,加之又无洗澡条件,身上长虱子,特别到了冬天,穿着空心棉袄,衣服缝里虱子下的蛋白花花,向一条白线一样。每当上山砍柴,身上出汗,虱子出来活动,咬的人浑身发痒,难受极了,我们一群小伙伴,坐在太阳下背风处,脱下棉袄捉虱子掐虮子(虱子蛋)。换洗的衣服水洗前先用开水烫一会,以期将虱子和虮子都烫死。那时好像农村小孩身上都长虱子,头发里也有这让人讨厌的寄生虫。
现在衣柜里挂满了四季换洗的衣服,衣服多了,还别说把哪件衣服穿烂,稍褪点色就穿不出来了。我有童年缺衣穿的经历,把旧衣服扔了吧,又实在不忍心。前年我听说四川凉山那儿还是很穷,冬天还有人穿凉拖鞋。我经一位朋友联系,接受捐赠衣服。我买了三个大蛇皮口袋,把洗干净的旧衣服给凉山那位朋友邮寄去,捐赠给了需要的村民。
4
我家在土改时被定为地主,一大院房子多半分给贫农,留下了三间正房、三间偏厦房。我父亲他们三兄弟,每人一间正房一间偏厦房。正房做睡房,偏厦房做厨房。房间不大,睡房安了两张大床,两张桌子和一个衣柜,剩下的空间就不多了。厨房里打了一个三口锅的土灶、墙角处一个火坑、摆放了一副带磨槽的手推石磨、支了一个案板、放了一个吃饭的圆桌,已显得挤挤挨挨。
随着家里人口不断增多,我母亲、妹妹、三弟睡一张床,父亲、我与二弟三人睡一张床,三个姐姐无地方睡觉了。睡房上面是木板楼,就在楼上支了两张床,三个姐姐上楼睡。只是晚上解手要从睡房那架木梯子上爬上爬下,另外楼上那几间相连正房之间无土墙壁,是用竹篾巴子隔开的。原来正房堂屋土改时分给了老家是宝鸡的钱姓人家,关中人习惯睡炕,一到冬天他家要烧炕,烟雾窜入楼上,熏得我三个姐姐无法入睡;夏天楼上不通风,离房顶太近,热得她们也无法入睡,时常哭哭啼啼向父母诉说。
我小学上四年级时,父母下决心要修房。生产队干部见我家住房实在困难,发善心同意批给建房地基,刚下好基础,有人向公社反映,说我家占用的是水田,驻队干部打招呼,房地基虽然是生产队、生产大队和袁家庄公社都批准了的,鉴于有人上告,无懒先停下工过段时间再说。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建房谈何容易?好在前几年我们生产队转为蔬菜队,吃粮由国家粮站按月按人头,每月25斤粗粮供应,吃饭有了保障。修土坯瓦房,首先要准备烧小青瓦,我家请来了几位山东人搬黄泥、做瓦坯,两万多页小青瓦做了近两个月,还没放入窑里烧,县民政局收容站以做瓦烧窑的师傅是自留人口为由,关入县收容站遣送回山东省原籍。烧一窖小青瓦,要不停火的烧三天三夜,要用山大一码柴火。砍柴火的重任就落在了父亲的肩上,一早一晚都要上山收柴,遇到星期天,我三个姐姐和我都跟着父亲去砍柴。柴收得差不多,山东做瓦的几个师傅又返回来了,装窑时找了十几个亲朋好友给帮忙,还要有酒有肉招待师傅与帮忙的亲朋。
小青瓦烧好了,接着要买檩条、椽板、过墙板等木料,大多都是在乡下买旧木料,一是省钱二是无需去批木材指标。这一准备就是三年,1976年春天正式动工,三间房打土墙,先请了一位打墙师傅把我父亲指导了一下,我父亲本是一介书生,生活逼的他啥农活都学会干了,这次又学会了打土墙掌板这种有一定技术的活。父亲有做宴席的手艺,周边几个生产队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要请我父亲去主厨,都是不收酬金给帮忙。我家修房打墙担黄土等活,他们又来给我家帮忙还活,省下了修房的人工工资。经过两三个月的辛劳,三间大瓦房终于建成,三个姐姐夜晚不用在那小阁楼上就寝了。
这几间房完全是父母在经济条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成的。2004年,我与三弟准备把当年土墙房拆除建成楼房,给父亲说了这事,他心里有些舍不得,这是他一生除了养育7个子女外的重要成果。拆房前,他让我大姐夫找了相机,爬到旁边山坡上照了几张照片。拆房那天,他也在帮忙搭手,看得出来他心里一直很难受。
5
父亲在生产队干活,挣得工分年底决算,一个工只值几毛钱,抵扣分粮款,往往还要倒给生产队找钱。可一大家人要生活,必须有一点零用钱,买个针头麻线、油(煤油)盐酱醋、牙膏洗衣粉之类的东西吧。我家院坝也有一棵大樱桃树,成熟后的樱桃个大汁多,到了5月成熟季节,父亲利用休息时间摘一些,装在大洋瓷盆里,旁边放一个杯子,装满一杯一角钱,就摆在我家门口。学校放学的学生、下班的单位职工,前来购买,家里可换的几元零用钱。自留地里多栽些葱,长成了挖出来偷偷地卖给工农兵饭店,也可换得一点零用钱。
上小学前,我就深切体会到钱对家庭的重要性。5分钱一斤的醋、1角钱一斤的酱油、2角钱一斤的盐,这些日常必需的调味品,让每一分钱都显得弥足珍贵。在县药材公司收购处,我认识了前胡和柴胡两种中药材。前胡根有小拇指粗,晒干后5分钱一斤;柴胡根细如香签,可晒干的柴胡能卖到4角8分钱一斤,就连柴胡杆也能卖8分钱一斤。
偶然发现我家旁边山坡上生长着这两种药材,我兴奋不已,背起小花篮背篓,拿着锄头就去采挖,第一次收获颇丰。回家后,我将前胡和柴胡从根部向上两寸处截断,去掉茎杆,洗净泥沙晾干,前胡杆直接丢弃,柴胡杆晾干后一并送到药材公司,竟卖了8角9分钱。这笔“收入”全交给母亲后,也激发出了我采药的热情,我几乎把那座山上的前胡、柴胡都采挖殆尽。自那以后,每年入秋,上山采药成了我的“固定项目”,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能采到的药材越来越少。
在袁家庄小学(现城关小学)读四五年级时,学校南侧正在修建佛坪县国营旅社。工地上堆放着从外地运来的青砖,放学后,我就去工地码砖。码砖是个技术活,需要把地面弄平整,一层铺20块砖,每5块一个方向,成正方形,共码12层,顶部再码10块,一摞砖总计250块,摞好后比我个头还高。码上层砖时,我得踩着垫脚的砖块才行。稍不注意,砖摞就会倒塌,只能从头再来。每天从放学码到天黑,虽然饥肠辘辘、疲惫不堪,但能挣到2角钱,回家还能吃到母亲特意留的饭菜,这些辛苦也就值了。此后,我每天放学都会去工地问老杨有没有砖可码。挣来的钱全交给母亲,我偶尔会留下一角钱,去买最爱的小人书。
中小学时期,每逢暑假,我就和小伙伴们到工地找活干,背沙、砸石子、搬运石头,这些都是按量计酬。建筑工地大多靠近椒溪河,沙石取自河道。将一立方米河沙背到工地,堆成四棱台形状,经管理人员丈量确认后,能挣4元钱。砸石子则要先把拳头大的石头从河道背到工地,按要求砸成特定规格,装满工地特制的正方体木框,大粒石子一方8元,小粒的12元。经常干这些活,要打领条去领钱,我在上小学四年级时,就对大写的一至十这几个汉字记得很清楚,领钱时要用私章,还花过两角钱在县五金联社刻过一枚。
记得县邮电局建房时,我们去搬石头。工地与椒溪河岸仅隔着一条公路,那天临近中午,我们三人用“抬秤”搬运一块套着铁丝圈的石头,从河滩往公路上走。当时没有河堤,也没有现成的路,只能沿着被河水冲刷得松软的岸边往上走。由于我们个头矮,石头被土坎垫了一下,从铁丝圈中滑落滚下,走在后面的我躲闪不及,小腿被划出一道两寸长的口子,鲜血直流。好在附近有生产大队合作医疗站,同伴赶忙送我去包扎。受伤后无法再搬石头,伙伴们也放弃了这活,那堆没搬完的石头只好送给了工地,而腿上的疤痕至今仍清晰可见。
那时单位上建房大多是土砖木平房。房角、墙壁交叉处砌砖柱,墙壁用水糊基垒砌。修房用水糊基的量很大,送到工地,一角钱一匹。暑假在我家准备建房的空地上平出一块地来,旁边挖一个两尺深、约三个平方米的坑,从官山坡跟脚挖黄泥用撮箕挑五六十米远,倒入土坑,土倒满再去小溪中挑水把坑里的黄泥泡发一晚上,第二天把泥和成浆糊状,平地上撒上一层草木灰,糊基匣匣(木板制,约两寸厚、一尺二长、六寸宽,矩形无底无盖方框)摆放在那,取一坨和好的稀泥放入按压实,手上醮水表皮摸成凹型,提起糊基匣匣,晾晒半干,立起来再晾晒。我们住街后,不通车全凭背和挑送往工地,甚是辛苦。
我家门前的凉桥巷旁,是庙垭沟小溪冲刷出的深沟,沟北面分布着县文化馆、文工团和县印刷厂,这些单位的垃圾都倾倒在沟里。袁家庄小学大门对面是县土产公司收购门市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这里收购牙膏皮,2分钱一个。那时的牙膏皮是锡制的。有一次,我在文工团的垃圾堆里捡到4个牙膏皮,卖了8分钱,并用这笔钱在新华书店买了本《草原英雄小姐妹》连环画。当晚兴奋得辗转难眠。自那以后,这几处垃圾堆成了我的“寻宝地”,上学放学路过时,我都会双眼仔细搜寻,不愿错过任何一个牙膏皮。
6
那时家境贫寒,父母从未给我们买过任何玩具。上世纪90年代初,我听过一位教育专家的报告,他提到如今孩子的玩具过于繁多,反而不利于培养发散思维和想象力。比如买一把玩具枪,孩子往往就只是当作枪来玩;而在困难时期,给孩子一截木棍,他可以把木棍端在手上当作枪,夹在双腿间当作马,举起来又能想象成一把刀……不过,这也只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但,可以肯定,贫穷无法限制人想象力的。
我小时候,最爱看《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这些战争题材的故事片(那时也没有更多影片可看)。男孩子大多喜欢玩具枪,可没钱买,我便自己动手制作。
我曾用木竹做过“响炮”。砍一根巴山木竹,截长短约5寸长一节和一根硬木棍,在木棍一端安上小竹节。接着,把纸放在嘴里嚼碎,取一小块塞进竹筒,用木棍将其推到竹筒另一头,再塞一小块,然后用力向前推木棍。随着空气被快速挤压,“呯”的一声响,前端的纸团就会射出去。现在回想起来,用嘴嚼写过字的纸既不卫生,射出去的纸团还有伤人的风险。
我还做过“水枪”。选取刀把粗细、七八寸长的竹筒,一端保留竹节,在中间钻一个火柴棍粗细的小孔。再找一根竹筷,在顶端缠布,使其粗细与竹筒内径一致,做成类似医用注射器的样子。将有竹节的一端浸入水中,拉动竹筷吸水,再向前推,就能把水射出数米远。那时,我们常分成两拨人,用水枪对射,玩得不亦乐乎。后来,邻居家的兽医送给我一个金属外壳、玻璃内胆的废旧注射器,用它来玩水枪,更是畅快淋漓。
最让我着迷的是自制的“火柴枪”。火柴枪玩起来需要两根火柴,发射时不仅有响声、会冒烟,还能射出“弹头”,十分逼真。制作火柴枪要用到四节自行车链条,当时全县就属县邮电局送报纸的邮递员自行车多,还有专人修车。多亏同学陈刚帮忙,他父亲在县邮电局工作,给我找来了四节链条。我用八号铁丝拧成手枪形状,把四节链条一端串在铁丝上,前面留一节,用固定自行车丝的螺蝐嵌入链条孔中固定,后三节用胶布缠紧。再取一根五号铁丝作撞针,插入链条上方的孔,用橡皮筋提供发射动力,还设计了扳机来控制撞针。使用时,将一根火柴头向内穿出链条,把另一根火柴头的火药刮入孔中,组装好后就可以射击了。做好这把火柴枪后,我喜欢得不得了,成天把它带在身上,上学也舍不得放下。有要好的同学想借去玩,我总是担心弄丢,没过一会儿就追着要回来。
记得有一天放学后,父亲让我去山坡上的自留地割苕藤,还要背一背篓回来喂猪。割苕藤休息时,我还拿出来把玩过。可等黄昏回到家,火柴枪却不见了踪影。我把家里和放苕藤的地方翻了个遍,都没找到。那一夜,我辗转难眠,连做梦都在找枪。第二天上学,老师讲课的内容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中午放学,我顾不上吃饭,一路小跑到山坡苕地里寻找。当看到它静静地躺在昨天放背篓的地方时,我悬着的心才落了地,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仿佛找回了自己的魂魄。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新建的电影院看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中途换胶片时,电影放映机出了故障,师傅们忙着修理,同学们坐在座位上闲聊。旁边的同学拿走我的火柴枪玩耍,突然“砰”的一声,虽然声音不大,却惊动了后排的语文老师。他径直走过来,把火柴枪没收了。我又气又急,直埋怨同学不该随意放枪。同学答应去向老师检讨,帮我把枪要回来。可过了一周,他虽然交了检讨书,枪却没拿回来。直到有一天,我当值日生给语文老师抱送作文本,发现火柴枪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我又惊又喜,趁老师不在,悄悄把枪拿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把它带到学校去了。
7
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缺吃少穿是常态,就连寻常可见的柴火也成了稀缺之物。按理说,我们家地处秦岭南坡的深山之中,漫山遍野皆是植被,不该为柴火发愁。可那时燃料单一,做饭、煮猪食、做豆腐、烧水,乃至冬天取暖,样样都离不开柴火。
我们生产队的柴山位于庙垭沟的两面山上。山坡和山沟的下半部,被开垦出来种粮;中上部则是砍柴的区域。山上的柴火以青㭎木、小橡子、麦稍子、大叶炮、红顺子、坏橡树等为主。若论哪种柴火好烧耐燃,上述几种木材依次排序,它们也自然成了砍柴的首选。儿时的我,几乎爬遍了这几面山坡的每一处地方,能砍的柴都砍了。再加上生产队和县建筑队开办的有砖瓦场,烧窑所需的柴火数量巨大,山上柴火的生长速度,远远赶不上生活需求的增长速度。
在我上中小学的秋冬时节,下午放学后、周末、节假日,乃至整个寒假,主要任务就是砍柴。我其实还挺乐意去砍柴的,可以约上几个小伙伴一起上山,既能砍柴,又能玩耍。有同伴相伴,自由自在,比起在家里听母亲唠叨,父亲喝斥惬意多了。天黑前,父亲收工回家,看到我砍回的柴火,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那一刻,我心里也满是成就感。那时候,我们下午放学早,时间与父亲回家吃饭不同步。每次出门砍柴,我就从苕窖里拿一个口感软糯、甜度十足的兰水苕,或者带上一根白萝卜,背上弯刀就往山上跑。饿了,就用弯刀削去外皮,啃上几口充饥。
到了星期天或是寒假,砍柴的收获就更多了,上午砍一捆,下午砍两捆。每座小山脊上,都有一条溜槽。那是因为砍柴的人太多,山坡又陡峭,大家顺着山脊往下拖拉柴火,不仅带走了泥土和小石块,再经过雨水常年冲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深壕。砍好的柴,用葛藤捆扎结实,顺着溜槽拖下山,然后再用肩膀扛回家。看着院坝边的柴垛一天天堆高,心里想着,这些积攒下来的柴火,足够春夏季使用了。当然,仅靠我一个人砍柴,远远不够家用。父亲有时会带着我和三个姐姐,集中两天时间,一起去砍柴。到了腊月的最后两天,父母会允许我把砍来的柴卖给砖窑,换得一两元钱,这钱归我自由支配,我通常会去买上一两包鞭炮,留着过年时玩耍。
后来,生产队的柴山几乎被砍光了,即便爬到山顶,也只能找到刀把粗的杂木。无奈之下,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椒溪河对面韩盘沟更深处的山坡。那里虽然能砍到小碗粗的木棒,可路途遥远,一天下来,也只能扛回一两根。而且,那不是我们生产队的柴山,一不小心,辛苦砍的柴就会被别人没收。父母不得不四处找人,把柴要回来。为了砍柴,韩盘沟的几面山,以及更远处的堰沟湾、梨房沟的山山峁峁,都留下了我攀爬的足迹。
8
童年的记忆如同褪色的老照片,即便过去了五十载春秋,那些浸透在贫穷里的点滴,依然在心底清晰如昨。
小时候,家境贫寒,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都写满了拮据。无论是生活所需,还是学习用品,都来之不易。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渐渐养成了珍惜物品的习惯,这一习惯,也成为了伴随我一生的财富。
记得上小学时,每年的学费不过一元钱,可就是这样一笔在如今看来微不足道,在当时却让家里犯了难。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家里实在拿不出这笔钱。一周过去,班主任发现班上还有几人未报名注册,便开始反复催促。多次催促后,仍有三人没交,我便是其中之一。想来是校长给班主任下了任务,那天,班主任神色严肃地对我们说:“明天再不缴费报名,就别来上学了。”我满心忐忑地回家告诉母亲,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只能无奈地继续等待。
第二天,我依旧没钱报名。面对班主任,我谎称家长借钱去了,保证明天一定交。可班主任没有丝毫通融,严厉地将我赶出教室,让我站到院子里。那时,天空正飘着细雨,不一会儿,我的衣服就被雨水浸透,寒意顺着脊梁往上爬。直到第二节课,班主任许是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有些过分,才让我站到教室后面。回到家,我把事情告诉母亲,她心疼得直掉眼泪。可即便再难,母亲还是四处奔波,不知向谁借到了一元钱,下午就赶忙带我去报了名。那位班主任,也因此成了我求学生涯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严厉老师。
在学习用品上,我更是精打细算。买不起作业本,就拿8分钱去县百货公司买一张白油光纸。回家后,父亲会用小刀将纸裁成32页书本大小。没有订书机,就用纸夹子固定,再用锥子在顶部钻出四个小眼,用包装物品的细纸绳仔细装订。看着父亲操作几次,我也学会了这门“手艺”。每次作业本写完,都要先交给父亲检查,确认没有浪费后,又才能得到8分钱买纸,自己动手装订新本子。为了把字写得工整,我还会找一张厚纸,用直尺画上通格,当作书写时的衬垫。用完的作业本,背面也绝不浪费,当作草稿纸继续使用。
文具对我来说更是奢侈,连最普通的塑料三角板都没有。上三年级学习几何知识,需要用到三角板、半圆仪、圆规,我只能厚着脸皮向同学借用。直到有一天放学,我在街上捡到一个黄色的30度、刻度12厘米的塑料三角板。这小小的三角板,从此便成了我最珍视的“宝贝”,陪伴我度过了小学、初中和中师的求学时光。即便后来我成为了一名教师,它依然安静地躺在我的案头,见证着那些艰苦却又充满希望的岁月。
那时的课本只有语文和算术两种,拿到新课本的我如获至宝。我学着姐姐们的样子,找来厚牛皮包装纸仔细包书皮。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字,我便央求他在封皮上工整地写下“语文”“算术”,再写上我的名字。在使用课本时,我格外小心,从不乱写乱画,哪怕有一点折痕,也要轻轻抚平。一学期结束,课本依旧崭新如初。
结语:如今,岁月的车轮已驶过六十五载,曾经的苦难早已化作滋养生命的养分。每当忆起那段贫穷艰难的童年,泪水总会不自觉地涌出。那些在困境中咬牙坚持的日子,那些与家人相互扶持的温暖,都成为了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谨以此文,致敬那个在岁月长河中奋力前行的自己。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