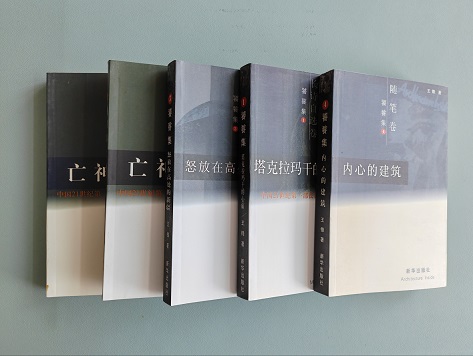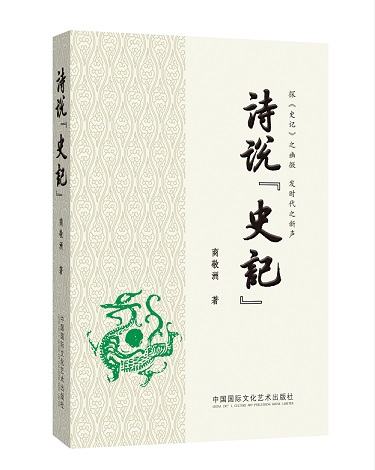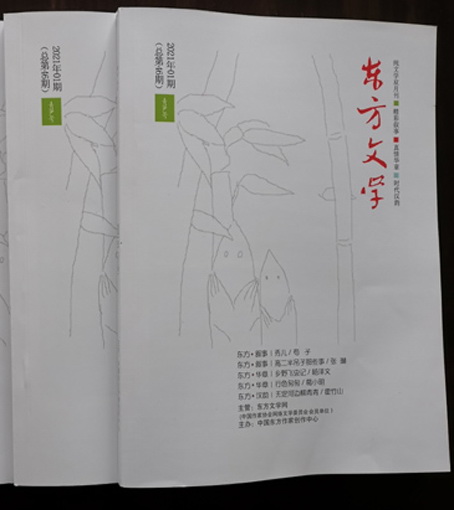《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以下简称《茶馆》)是历史学家王笛写给成都的又一封“情书”。绵密而生动的文字里,不仅寄托着远方游子对故土的思念,更蕴含着对城市历史、现状与出路的深邃思考。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茶馆》所书写的,虽只是现代中国百年历史流变中的一片微澜,却能于波光中见大气象,于方壶中窥大天地。茶馆业的百年沉浮,不仅是成都茶馆的百年史,更是中国百年生活变迁的缩影。《茶馆》涉及的议题包罗万象,比如国家对日常生活的介入与调控、人文城市研究的地方路径、微观史如何通向宏观史等。在诸多话题中,对于今日中国而言,书中提出的“恢复和保存中国的城市遗产”这一命题,似乎更为重要而迫切。相较于文学家对“百年乡愁”的执着书写,近年来因大规模城市改造、大片老旧小区快速消逝而引发的“城愁”,却鲜有学者给予关注。
如今,没人会否认保护城市文化遗产(尤其是城市文脉)对彰显城市独特性、促进城市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然而问题在于,相较于蔚为大观的国家历史叙述,城市历史叙述显得逊色不少,更不用说对城市文脉作细致梳理的著作了。此外,我们固然要呼吁回归城市传统,但值得追问的是:存在一种本质性的、一成不变的城市传统吗?还有,对城市遗产的保护该选择何种路径?是做博物馆式的“临终关怀”,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彰显其真精神?
保护城市遗产,关键在于保护城市文脉。然而,“恢复与重建中国城市的历史”实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城市文脉往往并非清晰可见,很多时候甚至隐而不现。如何抵达历史现场、如何筛选材料、采取何种立场叙述,不同的方法和立场所呈现的历史往往大相径庭。一条可行的路径是,历史学家尽可能占有丰富材料,秉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才可能接近历史现场。《茶馆》通过大量档案资料、新闻报道、文学作品,为我们具体而生动地呈现了以茶馆为代表的百年城市文脉的流变、曲折与发展。此外,作者借助田野调查,始终以平等的倾听者和对话者的身份,记录茶馆中形形色色的人,与他们随意交谈、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被调查对象最真实的表达”,进而尽可能清晰地呈现真实的生活样态,“保存其中最自然的东西”。
王笛注意到,自晚清以来,逛茶馆和打麻将常常成为被批判与改革的对象,其间遭遇种种外力冲击,从繁荣走向衰败,甚至一度绝迹。但改革开放后,即便经历了各种娱乐方式的激烈竞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逛茶馆和打麻将,“没有因为外来竞争而衰落”,“反而越加欣欣向荣,发展到了新的高度”。那么,茶馆为何能“在风风雨雨中仍然保持生命力”?王笛的观察是:第一,茶馆既是成都独特地理环境的产物,更深深植根于成都作为“天府之国”的独特地域文化。在这种地域文化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性。戏园、讲评书、自发娱乐……“喝茶韵戏,以心寄戏”早已成为当地人既定的、熟稔的活法。茶馆文化是独特地域文化与人心、人性的结合体,只要人心、人性未发生相应改变,即便因外界压力一时沉寂,一旦生存环境改善,这种生活方式便会迅速恢复活力。第二,市场经济激发了经营主体的活力。茶馆经营者能随时代变化不断调整经营方式:从最早使用留声机,到引进影像放映设施,再到设置私人包厢、提供麻将棋牌……他们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夹缝中求生存,总能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这种来自民间的自发力量,值得深入研究。第三,茶馆为城市公共生活提供了可以呼吸的空间。一个正常的城市社会,需要多元化的城市空间来接纳各类群体的社会交往、娱乐乃至生存需求,满足人们“更多、更丰富的公共生活的选择”。在《茶馆》中,茶馆不仅为进城谋生者提供了就业机会,还满足了城市居民的多样需求:它可以是俱乐部,是茶艺展演赛场,是国际象棋赛场,是麻将室,是婚姻介绍所,是文人聚集地,是媒体记者的“第二新闻现场”,也是信息中心……由此可见,茶馆在城市公共生活中承担着五花八门的功能,这种丰富性显然是其他空间难以替代的。
城市文脉既是一种空间与自然形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星罗棋布分布在成都街头小巷的茶馆,它首先是休闲、娱乐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喝茶、聊天、听戏、打麻将、交流信息,更承载着一种慢节奏的生活方式与处世态度。保护城市文化遗产,实质是在保护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文脉根植于城市的历史,隐藏在日常生活中,且始终对时代保持开放。当一种传统面对外来冲击时,唯有始终保持开放、对话的态度,才具有生命力。《茶馆》以丰富案例揭示:所谓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苟日新,日日新”的,是不断吸纳时代特质、持续被发明与建构的传统。那种对城市遗产“临终关怀”式的保护已毫无意义,城市文化遗产必须作为鲜活的力量融入城市生活;换句话说,只有在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中涤荡浸润,才能真正保护、激活并赓续城市传统。
一个有温度的城市,既要有烟火气,又要有人情味。烟火气体现在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里,人情味则体现在对外来者尤其是陌生人的接纳中,而这两者相辅相成。一个健康的城市社会,既要有私人空间,更要有像街角茶馆、菜市场、快餐店、口袋公园这样的“社会活动中心”。茶馆空间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容器,在当代文明转换的进程中,日常生活日渐成为城市精神、城市品格、城市软实力的源头活水。一个日常生活不够多元丰富的城市,不可能焕发真正的活力。因此,对城市文脉的保护,关键在于守护多样化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理应为各种生活方式留下足够的余地。
此外,王笛的叙事手法同样值得关注。《茶馆》既可以看作严谨的历史文本,也可以视为生动的非虚构作品。作者总能将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巧妙隐藏在冷静而生动的叙述中,这无疑得益于他兼具历史学家的严谨与文学创作者的笔墨功夫。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茶馆》中巧妙运用了大量档案材料、新闻报道,尤其是中外作家的笔记与手札,这些素材丰富了关于成都的城市记忆。城市精神借由记忆得以澄明,而记忆并非虚空。它的印记留在城市的每一处空间、每一件物体上,构成了人与城市之间深刻而隐秘的联结。城市精神不会主动呈现,甚至会如手纹般隐匿自身,需要发现者通过探寻去体认、辨识和打捞。因此,寻找城市精神的过程,正是展现城市记忆的过程。
如今,全球化的冲击让城市逐渐变得千篇一律。但《茶馆》告诉我们,瞬息万变的时代背后,隐藏着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在新的生活形态中,重新建立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都市生活的紧密联系,重新理解地方特质、构建面向未来的城市传统,在城市文脉中梳理过去与现在的关联、联通当下与未来,这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在这一点上,该书对茶馆的繁荣、消失、恢复乃至再度繁荣的细腻描摹,为我们赓续城市文脉提供了希望与可能。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