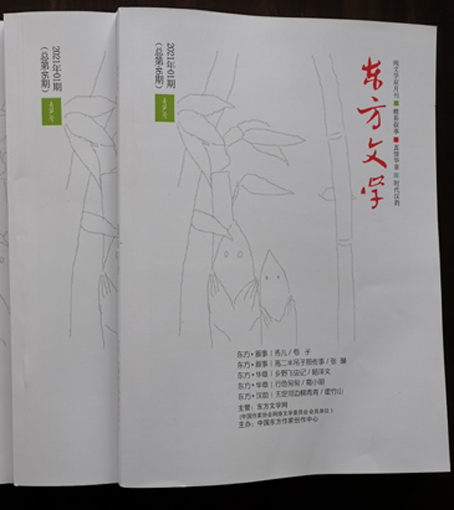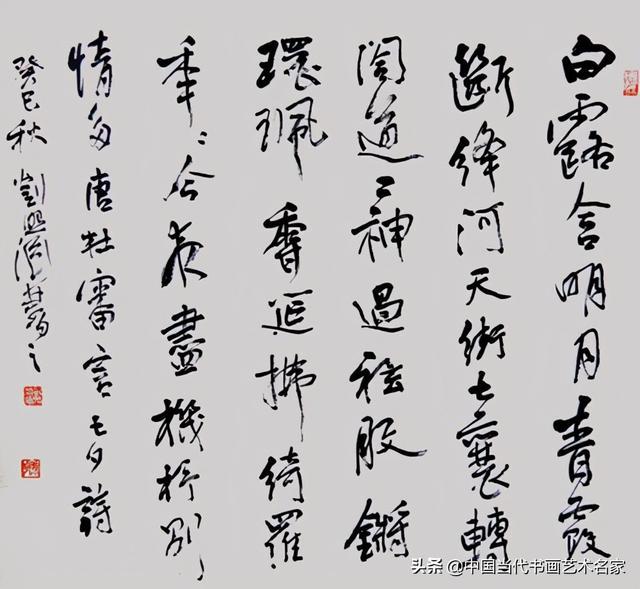我已经记不清来岳麓山多少回了。晨午夕夜,一天的每一段时光;春夏秋冬,一年的每一个季节;阴阳雨雪,气候的每一种变化;温热凉寒,身体的每一寸感知;爱恨愁怨,心灵的每一种情绪……我都在这里经历过,体验过。我以为已将全部的自己给了岳麓山,也以为已把岳麓山的全部装在了心中。
可今年,等我把有关岳麓山的书籍一部部读下来后才发现,过往我熟悉的,只是岳麓山的表象,是视野范围内的岳麓山,是空间里的岳麓山,是时间截面上的岳麓山。它最多是以一年为轮回单位,春夏秋冬,重复变幻。而岁月纵深处的岳麓山,则被我和大多数游客忽略了。
据史载,长沙有上万年的文明史,两千五百年的建城史。在春秋时代,这里就有楚城。而更早的西周王子,可能就是从麓山渡江,去往宁乡,建立大禾方国。秦朝征伐岭南的五十万将士,溯湘江而上,在这里驻扎过。汉代刘氏皇子分封长沙,落地生根,自成王国。文明的星光,点点汇集,照亮三湘大地。
自屈贾以来,无数谪臣墨客、三教九流来往于这里,不知留下过多少慷慨激昂、悲欣交集的故事。山水洲城将这一切永久地封存在了时光隧道,史册与记忆却只能挂一漏万,事过境迁就再也无法追寻。如今,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幽居长沙三年的贾谊及无数曾入驻古城的重臣名流,是否登过岳麓山?即便是有麓山诗文的名家,许多也只能躺在故纸堆里,任流光之尘,寸寸掩埋。
尽管在空间上,我们离他们是如此之近,若能缩年成秒,大家或许都可以摩肩接踵了。然而即便是如今的科技,也只能缩短空间的时距,无法破开时间的阻隔,在光阴之河里,哪怕是上溯一秒,我们都做不到。无数前行者,就这样孤独停留在岁月的尘烟里,不为人知。
有多少游客知道,岳麓山曾来过杜甫、韩愈、柳宗元等耳熟能详的诗人,来过辛弃疾、李纲、文天祥等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英雄,来过怀素、米芾、郑板桥等书画家?匆匆过客,如雪泥鸿爪,转眼就消失了。极少数人会留下诗文,极个别人会在山中摩崖刻字、建亭造楼,然而兵燹一过,一切又全被清零。
况且,古代建筑以木料为主,少用石头堆砌,而南方天气潮湿,雨水频繁,植物疯长。即便是在和平年代,只要疏于打理,那些伫立在丛林里的木质建筑,也经不起长时间的风雨漫漶、藤蔓缠绕、虫蠹蛀咬,很快就会颓败、坍塌、腐朽,归于尘土,湮于草木,仿佛从没存在过。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今年的岳麓山不是去年的岳麓山,明清的岳麓山不是秦汉的岳麓山。每一个历史时期,岳麓山都有它不同的面貌。如今它植被繁茂,古木参天,春日新绿盎然,夏天满山青翠,清秋层林尽染,凉冬碧黛如玉。每一座亭阁掩映其间,都如画龙点睛。
不少游客或许会以为,岳麓山一直都是这样。然而并非如此。在抗战时期,为防日寇偷袭,除清风峡附近的林木有所保留外,其他植株曾被刈除一尽。再往历史深处望去,南宋初年,抗金名将李纲登上岳麓山巅时,看到的是金兵过后,长沙遍地瓦砾,少有人烟。林木焚尽,原野山冈光秃如剃。除两三座古刹外,其他包括书院在内的所有建筑都被摧毁。
由于人口增长、耕地扩张、荒野萎缩、林木减少,北宋时江浙一带,柴薪已难以为继。长沙地势平坦,周边都是良田,唯西部点缀几尾山峦,是整个城市燃料的最大供给地。自宋代以来,除了岳麓山庙产,周边山林很多时期都被砍得精光。想来,生态文明的提出,还需要强劲的科技做后盾。若没有新能源的及时开发,按长沙现有的人口,岳麓山或许早已寸草不生,连柴蔸茅根都会被挖出来当燃料。
如今的岳麓山已是草木深深。我想,若是能沿岳麓山脚修一条文化步行道,每隔一段距离竖一尊名人塑像,并刻上他们的诗文,那么附近的市民,是否便能在散步中闲谈诗文,更方便地追忆前贤壮怀激烈的往事?如此,或许时空纵深里的岳麓山,将会在更多人的心中熠熠生辉。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