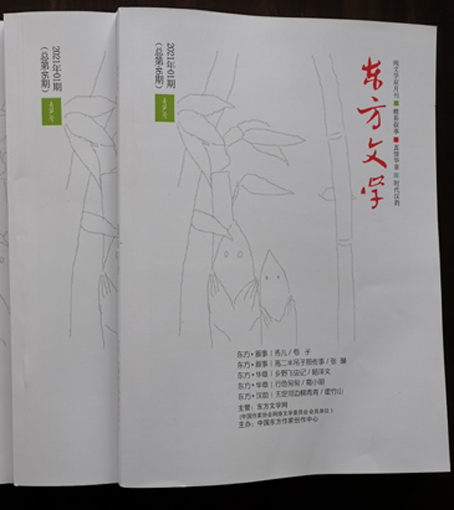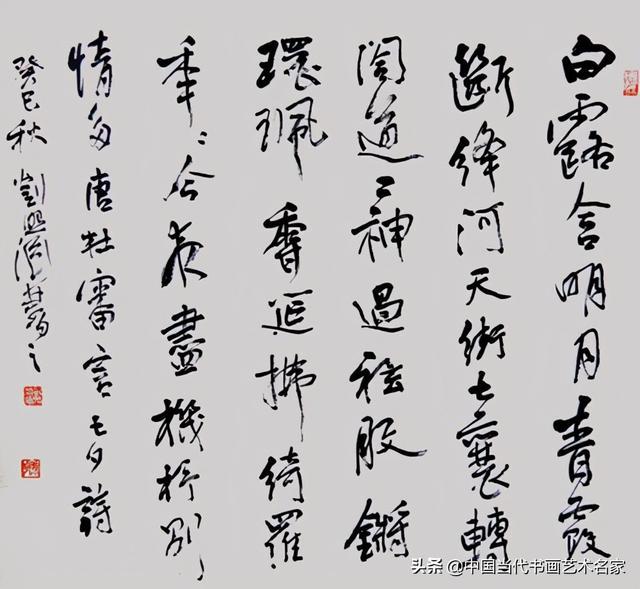大运河的水,千年如一日地流淌,滋养着两岸的生命。春来夏往,万物竞发。晨光里,人们舒展腰肢,各练各的招式。而岸边的新竹、芦苇和茅草,随风起伏,各自诉说着生命的语言。
新竹最是夺目。一场春雨过后,它们便从黝黑的老竹林里破土而出,青翠笔直,节节攀升,仿佛要刺破蓝天。竹节处还带着湿润的泥土气,在阳光下泛着淡青色的光晕。不过几日,它们已高过母竹,顶端几片嫩叶在风中瑟瑟摇曳,像初生的雏凤抖擞羽毛。老竹沙沙作响,似在叮嘱,又似在惊叹。新竹却只管向上,那股势头,仿佛要带着整片竹林飞向云端。偶有飞鸟掠过,误将这挺拔的新竹当作登天的云梯,轻轻一歇,又振翅而去。
运河的水面映着这新绿,波纹里浮动着千万柄翡翠剑影。最妙的是顶端新叶,如缀上的碧玉片片下垂着,在风里轻轻摇曳,影子投向水面,与往来的船影嬉戏。老船工撑篙而过,见了此景,不由放慢动作,生怕惊破了这静好的时光。
然而,并非所有的生命都如新竹这般锋芒毕露。
芦苇生长在浅滩上,也学着竹子的样子,努力向上伸展,可终究不够高,也不够刚。才抽出一半的穗子在风中轻轻摇晃,不久便要开出一蓬素白的花。它望着自己水中的倒影,纤细、柔软,与竹的挺拔相比,不禁黯然。
旁边的茅草却伏在地上,叶子枯黄,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安然守着自己的位置。它不与竹子比高,也不与芦苇争强,只是静静地匍匐着,让飞鸟停歇,让虫蚁藏身。
这时,一群鸟儿飞来,在芦苇和茅草间跳跃,啄食草籽,又忽而振翅,在低空盘旋。一只黄莺落在芦苇梢头,歌声清亮:“何必羡青云直上?我的歌声只在芦苇荡里回荡……”
是啊,天地造化,本就不拘一格。竹有竹的凌云志,苇有苇的柔韧美,茅草虽低,却为大地披上衣裳,成为那蚁虫的游戏地,飞鸟着陆的繁殖场。正如人世间,各有各的位,各有各的为。显赫者有显赫者的风光,平凡者亦有平凡者的自在。位高者未必心安,位卑者未必不乐。
但无论如何,生命总该向上。竹要拔节,苇要抽穗,茅草也要在秋风中结籽。人亦如此,无论身处何位,都该尽力生长,不负此生,亦不负这世间。
大运河的水千年如斯,默默见证着两岸的生命轮回——高耸的,低伏的,刚直的,柔韧的,都在它的波光里找到了存在的意义,化作永恒的生命絮语。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