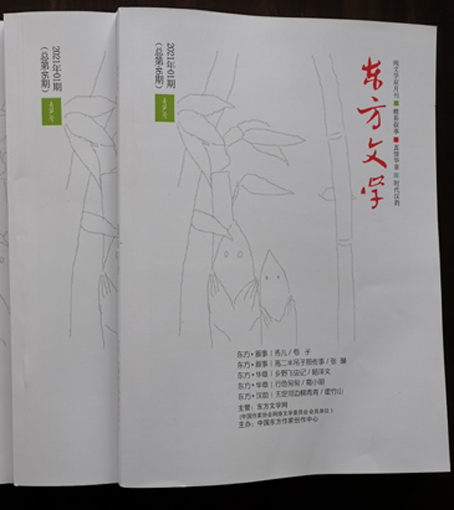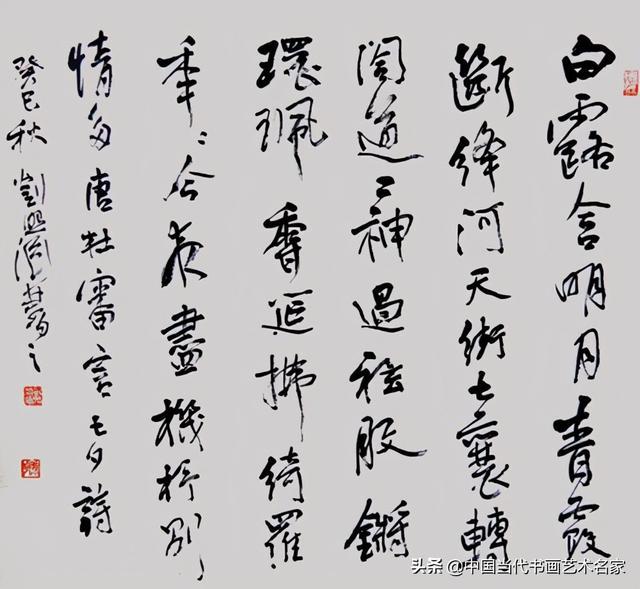一提起马蜂窝,人们总联想到"乱子"。生长在这里与蜜蜂样貌相似却不让待见的飞虫,蛰过不少农村孩子,也深深蛰进了他们的记忆。我对马蜂怀着复杂的情感,说不出是喜爱,还是厌恶,而是一种历经岁月沉淀后的理解与反思。
这些年,马蜂的踪影日渐稀少。今日清晨,在运河畔的弃置多年的老砖垛间,与它不期而遇。
晨光熹微中,我沿大运河散步,在石佛闸南的河东岸,远远的就看见几垛百年青色古砖随意堆叠,这是老城拆迁而来。杂草蔓生其间,就在这荒芜之处,砖垛转角悬空处垂着几个马蜂窝,其灰褐色与古砖浑然一体。若不细看,极易错过这自然的杰作。蜂窝上静静簇拥着红黄斑纹的马蜂,它们对我的靠近拍照无动于衷,偶有翅膀煽动,似风吹过。
这意外的重逢,唤醒了尘封的童年记忆。
儿时的乡村,马蜂窝是屋檐下、枣树梨树间的寻常景致。惊蛰过后,它们便与北归的燕子一同,开始一年的营生。我家过道房的顶上,常有马蜂筑窝。夏日里,我穿着小裤衩,躺卧在汗水浸得泛红,阴凉光滑的秫秸席子上面,享受着过堂的风凉和蜂鸣入眠、写作业。这时候,观察马蜂筑巢也是极富趣味的事情。三两只先锋选好避风的檩条,打下基桩,不出三五日,那处便由黄转黑,渐渐隆起,最终形成倒悬的莲蓬状蜂房。待孔洞初现,马蜂便日渐增多,蓬房围得密不透风。"围得跟马蜂窝似的"这句乡谚,确是生动。
还有一种色黑个大的,我们叫它土蜂,其声嗡嗡,时远时近,我常屏息聆听,声音一旦停止,就会快速折身寻其踪迹,时见它正钻入土墙孔洞,或飞进它营造的花生型泥巢。过道顶上还有燕子窝,燕子筑巢、育雏、飞来飞去捉虫投喂、雏燕探头张嘴接食和出巢亮翅的样子,会让我看的发呆并引起我无尽的遐想。燕子和马蜂的窝相距不远,互不相扰。父亲说,这是家蜂,你不惹它,它不会伤人的。还说,万物有灵,人丁兴旺之家,才会有生灵来住。我真还相信,从不惊扰它们,在孤寡人家的屋檐,似乎真的少见它们的行踪。
但也有意外。记得一年夏天,我刚剃了光头,去村外水坑冲洗。抬头见坑沿上的梨树,一时兴起便赤条条攀了上去。手指刚夠到那只惹眼的大梨子,忽觉前臂刺痛,原来触动了正在啃梨的马蜂。这"护果使者"毫不留情,旋即回身又在我光头上补了一针,疼得我险些坠树。伤口经污水浸泡,竟化脓月余才癒。
说来也巧,之后在这里,我瞥见一只马蜂落在水边煽动着游走,那红黄相间的斑纹,像极了蛰我的那只。我岂肯放过,悄悄挖了一把渍泥,正要投掷,它却振翅飞走。我注目看它的落处,追出水坑,竟在生产队放大车的屋后檐下发现了它的巢穴。情急之下,我一把扯下裤头,双手执撑着,蹑手蹑脚靠近,对着蜂窝猛得一裹,迅速下坑连泥带水一通揉搓。看着仅有几只仓皇逃窜,我那"大仇得报"的快意,至今想来犹觉可笑。
如今砖垛间的马蜂,引发我更深层的困惑:为何它们舍弃了传统的屋檐树木,选择这荒僻之地?诗意地想,或许是这些来自老宅的古砖,召唤着马蜂寻根;或许我家的老马蜂,不远百里来守望故友。而科学的解释则是,现代建筑的化学物料与果树的农药,人们虽没有觉察得到,但敏感的它们无法忍受,只能节节败退,寻找仅可栖存缝隙,将至绝境。
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种古老的共生智慧在今天显得尤为珍贵。父亲那辈人朴素的自然观——容忍燕子在八仙桌上排便、欣赏马蜂在屋檐下筑巢——暗合了深远的生态哲理。本能地理解,人类不过是生命之网的一个节点,而非主宰。当我们将野生动物简单划分为"益虫""害虫"时,已经割裂了万物互依的天然联系。
社会的“进步”,摧残了自然生命。为灭蚊蝇喷洒杀虫剂时,未料想会毒杀传粉昆虫;固堤硬化河道时,不曾考虑水草消失会让鱼虾无处产卵。顾此失彼,割裂了生态。城市公园的案例像一记警钟。 五年前,管理者为追求"整洁美观",砍伐灌木、清理杂草、频繁喷洒农药。结果呢?飞鸟因无虫可食飞走了,芦苇丛消失后水禽无处隐身也不再落脚。拍鸟爱好者至今困惑,为何环境改善了,那片大湖再难重现2015年冬日数百只天鹅齐栖的盛景?这些细节残酷地证明,对生态治理顾此失彼,所谓的"保护"沦为精致的破坏。
砖垛间的马蜂如同沉默的预言者。它们的消失与重现都在叩问人类的文明选择:我们究竟要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是将自然彻底改造为人类独享的堡垒,还是保留万物共生的弹性空间?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灰砖与蜂巢的偶然相遇中,最古老的建筑材料与最古老的生命形式,在现代化的夹缝中意外重逢,提醒我们回归平衡的可能。
归途中的运河波光,让我想起老家的水坑,过道里的燕子和蜂巢。现代环保最需要的,是超越"益害二分"的整体观,象几十年前除害时被捕杀的野兔麻雀,现在成了受保护的动物。保护要讲究系统性,如燕子不能只留它的巢穴,还需容忍它觅食的飞虫有在;修复湿地不能只关注天鹅,还要呵护滋养浮游生物的淤泥。就像中医调理气血,生态健康需要动态平衡。留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可能比人工草坪养活更多生命;容忍马蜂在砖垛安家,或许比强行"移植"到保护区更明智。当我们学会在"人类需求"与"自然逻辑"间找到平衡,才是文明真正的进步。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