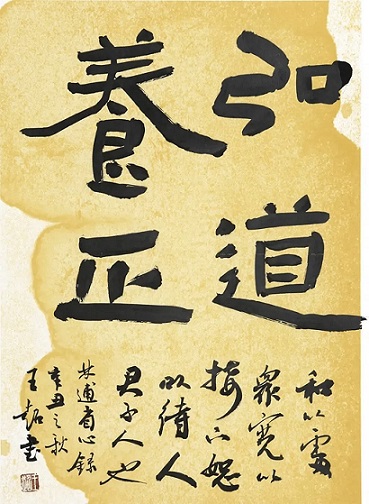刘德茂老汉一住进医院,才知道五个儿子,各有各的难处,他们的日子都有黑洞,不过是洞的大小深浅不一样罢了。
老汉的四儿子刘四民是凤山县民政局办公室主任。他要处理的事务象牛毛一样繁杂。5.12地震后,同为重灾区的陈宝市凤山县民政局的各个股室紧张的象备战一样:灾民建房,社会救济等事无巨细,都得他审核了才报呈局长签字。地震快过去两个多月了,有些乡镇还因危房、漏房审核的问题来民政局讨说法。他刚刚打发走几个村民,就听到打字员小张叫他。刘四民扔下手里的文件,接过电话。他将听筒轻捂在耳朵上,直起腰身,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然后嗡声嗡气地问,喂,你是谁啊?电话那边理直气壮的声音直冲进他的耳朵:我是你爸!
刘四民一激灵,赶忙弯下腰身压低了声音问,爸,咋啦?有啥事?电话那头的父亲清了清嗓子,停了两秒钟,才说,你有时间么?刘四民问,咋啦?有啥事你赶紧说嘛。你有时间了回来一趟能行啊不?父亲迟疑地说。四民似乎知道父亲的要说什么,就埋怨父亲说,你又要给谁帮忙啊。我说你就别管人家的闲事。刘德茂老汉最得意的就是四儿子四民了。自从四民进了民政局后,他逢人就说,我四儿在县政府上班呢。自从地震后,那些拐弯抹角的亲戚都跑来要灾民建房指标。他大舅家表姐的儿子在地震来临时,为了逃生,从三楼教室跳下,摔断了腿,住进了医院,来找他要求赈济。他很乐意就把这事给办了。可是有些人家的房是地震前拆的,硬要算到地震头上,就引起了民愤。前几天,一个远房叔叔懒惰了半辈子,仍住在土坯房里头,现在要盖新房,他也给通融了。父亲这次又揽了什么让他棘手的事儿?
刘四民随口问道,爸,你好吗?我妈好吗?
那边上声音低了下去,不好,要你回来哩。刘四民一听,吓了一跳,平时他惯常地问他们好不好。父母总是说好,好着呢。这次父亲能说不好,可见是真的不好了。父母都七十多岁的人了,身子骨都还算硬朗。自家种两个人的二亩地,养两只羊,还带着弟弟五民的孩子。五民两口子去南方打工去了,将儿子放家里。眼看两老人作务不动庄稼了,五民还没有回来的意思。平时家里的大小事都由四民给张罗着。有事了就周末回去,没事了就打个电话问问。农忙时请假回去,帮父母收种庄稼。父母精精神神的,四民也就放心工作。想想父母将他们弟兄五个一个个拉扯大,又供四民上了大学。如今,四民在县里重要部门工作,且工作得心应手。平时又能照顾上父母,再忙再累,看见疼爱自己的父母,他的心理都是暖乎乎的。父亲的电话,让四民的神经又绷紧了。他紧握住电话听筒,又问了几次啥事,想从父亲的声音里获得些话音儿。父亲只是说,你这个周末回来啊。你回来了我有事跟你说。
爸,啥事?你说啊。四民被父亲的吞吞吐吐弄得更加紧张。
啊,你回来了再说。你早点回来啊。父亲的语调又低又沉。说话拖音很短,没有一点气力。四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然后说爸,你放心,我星期五一定早早回来。
这几日,刘四民正和妻子郝彩虹闹别扭。遭遇了罕见的大地震后,县民政局和科技中心在县政府大院里搭起了防震棚成立了防震救灾指挥部,县长抽调了刘四民为防震办公室主任。5月12日以后,余震不断,全县处于紧急预警状态,县城各主要街道两侧都搭起了防震棚。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在机关大院里也搭起了防震棚。四民被安排在防震办主持日常事务。轮到他值班时得二十四小时坚守岗位。他给在县东关小学教书的妻子发了个短信,让她照顾好儿子刘早。他又操心父母。就抽空回村里给父母在街道上搭了个防震棚,让父母住进去。他一旦工作起来,就把家里的事儿给忘了。后来,妻子打来电话,说要跟他离婚。他才想起冷落了她娘俩。郝彩虹一生气就会绷着一张脸,整日不说话不理会任何人。恁四民的话再温暖再可心她都不言不语。刘四民只好哄儿子,让儿子去逗妻子。做母亲的跟谁生气也不会跟自己的孩子生气。爷儿俩一唱一和,一起哄郝彩虹。好不容易将妻子哄得眉开眼笑,他才动手干起了家务活。将娘俩安置在县政府院里的防震棚内。
紧张而惶恐的一个月过去了,四民已是身心疲惫。回到家里,妻子这边总要陪上笑脸,儿子刘早受了惊吓,总是做恶梦。自从主管社会救济的副局长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他的事儿都摊到四民身上了。他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刚到三十五岁,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三夏大忙季节,他好说歹说让妻子回家帮忙收麦子。郝彩虹和刘早在家烧水做饭,四民和父母将二亩麦子收割回来,摊场碾打完毕,又种上了二亩玉米,给辣椒培了土,才算了结了一年中最繁重的夏收工作。父母年迈,家里大事小事都得四民去张罗。就是买袋食盐,买包感冒药都要他从县城买回去。父亲年纪大了,上一回城要攒好几天的力气。母亲眼神不好,在家里做饭打扫等轻来去轻去的活计还可以,城里车多人多,出个啥事谁受得了。父亲一向健康硬朗,只是越来越衰老,重体力活干不了了,抵抗力也下降了,头疼脑热的,他得见天地往回跑。这次父亲打来电话,也没说啥事,但从他的口音上四民听出了点什么,他的心里越发的瞀乱。他盼望时间的脚走快点,到了周末带上媳妇儿子回老家看看。他的心事全写在脸上了,心不在焉,丢三拉四,在家里闷头抽烟。惹得郝彩虹一个劲埋怨,咋了,把魂丢了吗?看你那德行。去把地板拖一拖。郝彩虹递过拖把,四民没接着,拖把把儿落下来,打在儿子刘早的头上。刘早哇地一声大哭不止。郝彩虹的脸都绿了。她抓起拖把朝四民的腿上撸。四民跳开了,顺势躲进了卫生间。郝彩虹边哄儿子边骂,刘四民,我瞎了眼了嫁给你,你成天到晚不着家不说,回来了也不帮我干家务,也不带孩子,你整天象丢了魂似的。你都想些啥?我看你的心思就没在我娘俩身上。你那老爹老妈不只你一个儿子。要你一个人逞能耐。他们养了五个儿子,老了大伙都得管。凭什么让你一个人摊这些破事啊。你贴钱就算了,还不停地往家跑。老大、老三不是在家吗。他们当哥的也得管。我跟了你真是倒了大霉了。说着,就呜呜咽咽的哭开了。
刘四民最怕的就是女人的眼泪。郝彩虹那大颗大颗的泪蛋子砸得他心疼。他连忙跑出来,抱住郝彩虹连挠带搡,费了半天工夫才将媳妇儿哄高兴了。刘早已经歪在沙发里睡着了。他一把揽过媳妇,将她抱进卧室,手探进她的衣服里摩挲。这个时候,只有叫下面说话才能哄住妻子。
刘德茂老汉一吃完饭就站在大门口朝西望,他屏气凝神,仔细瞅着走来的每一个人身影和走路的姿势。在家门口看了半下午,仍然不见儿子四民回来。他就踅到村口,蹲在路边的大柿树下,盯着每一辆从北边开来的乡村公交车。如果有哪一辆车在村口有减速的迹象,他就赶紧站起来。眼看天就快黑了,最末一班车都过去了,还不见四民的身影,他拿出磕过几遍的烟袋锅子,使劲地在地上磕着。他扶住身后的树干站起来,两条腿僵硬又麻又酸几乎迈不动步子,左脚象踩了棉花似的没有一点力道。刚一站起来,他头晕得厉害,就扶住大树闭上眼睛缓缓神,过了一会儿,眼前的金星不乱飞了,他才慢慢地挪动步子往家走去。等他回到家里,天色已经黑尽了,他困倦得连眼皮都不想抬,就一头栽到炕上,长长地叹气。
刘四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知道父亲遇到了难怅事了。他的心里就象被一块大石头压住了,急切地等待着周末。星期六早晨六点,刘四民早早地爬起来,给妻子儿子买来早点,自己抓了根油条就上了回老家的公交车。
牛芝莲一见四民回来了,就一把抓住儿子的手,眼泪汪汪地说:四民,你咋才回来啊?你爹盼你回来。昨天在路口等到天黑了才回了家。四民接父亲在炕上躺着,心里一惊。父亲是个勤快人,从来没有睡过懒觉。父亲的身子一向很硬朗,没有被疾病撂倒过,今日却盖得严严地躺着。四民扑到炕上,抓住父亲的手问:爹,你是咋了?你甭吓我。他的声音急切而枯涩,带着点哭音。刘德茂挣扎着爬起来说,地震以后,我老感觉头晕晕的,脚象踩到棉花团上了似的发软。我老感觉还像地震哩,就没当一回事,这几天浑身无力,啥都不想弄。四民安慰父亲,爹,你甭怕,那是地震后遗症呢。头晕是不是血压高了。腿软呢,可能是缺钙。好了,吃完饭,咱到县医院去检查检查。别担心,有我呢。一听儿子说放了口话,刘德茂一骨碌爬起来要吃饭。牛翠莲递上热好的一碗羊奶,羊耐里泡着锅盔馍。看着父亲吃喝完了,四民领着父亲进了城。
到了医院,做了CT检查和血脂化验。医生说,老人的脑子里有四处腔梗,差一点点就堵住了要害部位。赶紧住院吧。四民一听头就大了。自己怎么粗心到这程度,父亲病成这样子了,都还不知道么。父亲万一要是跌一跤成了偏瘫,问题就大了。医生仔细端详了刘德茂,然抓住他那不停颤抖的手问:老人的口鼻歪斜有多长时间了?这双手是不是刚开始颤抖?四民说,我爹手抖这病,时间长了,也没当一回事,我们太粗心了,没有发现口眼歪斜么。医生埋怨四民,你们这些当儿子的粗心大意得很,老人的情况这么严重,竟然说才发现。快去办住院手续。
医生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将四民的心戳疼了。随着年纪增大,父亲的手颤晃得特别厉害,甚至端不住碗,握不住筷子,通常一碗面条抖抖索索地吃不到嘴里去。每次回家看见父亲颤抖着双手,端不住碗,夹不上菜,四民的心里就像被无形的大手狠劲地揉搓着。他常劝父亲去看看医生,父亲总说,不碍事,你爷的手也是这样子。或者以家务活太多,没有时间为由推脱着。四民懊恼内疚,自己工作再忙,也不能将父亲的病忽略了呀。恐惧和懊悔在他的体内蔓延,一下子就充塞了他的毛细血管,他的口腔泛上了一股苦味。是没有时间吗?他没有陪父母的时间却有陪人喝酒打麻将的时间。他把大把的时间花费在了上网聊天和无聊的应酬上,花在陪妻子逛商场做美容上了。办完了住院手续,四民的手心里冒出了汗滴。他将手伸到眼前仔细看了看。这双手,会不会老了也颤晃起来?好象在一眨眼的工夫,父亲腰身就这样驮了,人就像脱水的蔬菜一样蔫巴了。四民不敢去想。窗外阳光很好,父亲在阳光里的身影越发的瘦弱和孤单了。
刘德茂住进医院。刘四民第一个想到的是应该给三个哥哥打个电话,毕竟父亲住院是大事。自从他上了班,就将父母的穿衣看病行情送礼的日常开销等都揽了过来。他觉得,自己是弟兄五个中唯一吃公家饭的,每月都有固定工资。兄弟们都挺不容易的。大民老实,没有别的手艺,在家作务着几亩田地。可是,化肥、种子、农机费等价格日益上涨。辛苦一年,也落不下几个钱。二民做水果批发生意,起先没有赚下钱。后来生意做大了,做到省城去了,一年半载回来一会。三民两口字供着俩个高中生,每周都得五十、一百的给钱。两口子一忙完地里的活,就到城里建筑工地上干去了。父母跟着弟弟五民过。五民去广州打工,五六年回来了一回。他领回了媳妇,生下个胖儿子。儿子还没过周岁就给父母扔下了。父母在家,要种四五个人的地,还要照看五民的孩子,喂着羊和狗。两个七十多岁的人,整天手脚不停地忙活。父亲看着精精神神的,谁知却潜藏着如此大的疾病。三个兄弟一听父亲病了,都在电话里咋咋呼呼地嚷。大民说,爹病了?啥病?不是一向都好着么?四民,你先在医院看着,我有时间就来。二民说:咋了?爹病了,你赶快给五民打电话,让他回来。我很忙,生意上的事脱不开身。要多少钱你说一声。啥,我出了钱还要出力。我很忙。大民和三民不在家吗?给他们都打电话。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你给他们较真清楚。
四民一听二民的话,心里就越发堵得慌。他给大哥二哥打电话的意思,一是先告知病情;二是试探他们的态度。没想到在外面干了这么多年事的二哥说出这样生分的话。他赶紧挂了电话。但是二哥在电话那头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天际刮来的大风,一恍惚就把四民吹懵了。他觉得自己束手无策,不能去依靠任何人了。三民索性说,四民,你在城里看着办。我有时间了就来看父亲。听了老大、老二、老三的话,四民哑然伫立。他觉得自己找不到一句恰当的话来回答他们,干脆关了手机。他将父亲安置在内科病房里。医生给挂上了的吊瓶。他去单位向局长请了假。局长让他时刻开着手机,如果有特殊情况就得来单位处理。
刘德茂躺在床上,紧闭眼睛,右手上打着点滴。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有规律地往下滴落。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医院。他的神色黯淡无光,脸色蜡黄蜡黄的,脸颊上的老年斑使得他原本清癯的面容疲惫而衰老。掉光了牙齿的嘴巴深深地塌陷下去,使得他的脸比衰败了的菊花还萎蔫。花白的胡茬无精打采地聚在皱缩的嘴唇周围,只有浓密的眉毛在耀眼地支棱着。打着点滴的刘德茂格外的安详和孱弱。他的胸脯在微微地起伏,晶莹而透明的滴液滋润着他干巴而老迈的身体。
看着父亲虚弱的样子,四民突然有些想哭。他擤了擤鼻子,干咳了几声,将泛上心来的苦味向下压。他坐在床边,抓住父亲的一只手。那只如衰败的枯树枝也长了老年斑。他稍微用力握了一下父亲的这只手,这只手在四民的手中轻轻地颤抖起来。父亲的身上散发出淡淡的旱烟味和汗臭味。父亲发出了轻微的鼾声。他太累了。四民的脑子有些模糊,心里好象被烂棉花塞住了似的郁闷。父亲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能好好歇下。不经意间,父亲就已经七十四岁了,就已经这样老迈了。他静静地躺着,仿佛是匆忙跑了一程,终于跑到了医院,可以放心的睡一觉了。
手机的吵闹打破了病房的静谧。四民一听,是二民的声音:爹的情况怎么样啊?要住多长时间?四民你多费心。我有时间了尽量就回来。
你快点回来吧。生意上的事先交待给嫂子。我单位这两天很忙。四民说。
好的。看来我不回去是不行的了。四民,你先照着啊
四民知道二哥不可能就回来,就耐下性子看着父亲将滴打完。刘德茂刚将针打完,儿子四民的手机就响了。他赶紧叫儿子去单位。刘四民回到单位,处理了几件棘手的业务。他又给局长说:我爹住院了,中午我要在医院里陪护。下午没事了我来单位处理业务。局长阴着脸,一声不吭地抽烟喝茶。局长办公室的空气象凝固了一般,四民仔细聆听着局长的鼻息声。等局长慢条斯理地抽完了一根烟,颇不耐烦地朝四民挥了挥手,说,行,你去吧。四民紧攥着的手心沁出了汗水。
郝彩虹领着儿子刘早来医院看望公公来了。刘早一见爷爷,就偎进爷爷的怀里撒娇。刘德茂最疼爱的儿子是四民,自然就越发心疼孙子刘早了。刘早掰下一根香蕉,剥了皮喂给爷爷。一会儿,他又脱掉鞋子,爬上病床,坐在爷爷的腿上,。刘德茂一看见孙子刘早,心里的病去了大半。
刘德茂终于闲下来了。他躺在病床上格外地想家,想起了自己的亲戚朋友。能来的人都来探望来了,躺在医院里,看着亲戚的笑脸,听着安慰的话语,他的心里倍感慰帖。牛翠莲来了。她一看老伴躺在病床上打点滴,就两眼发红,说话的声音发抖。她在医院陪护了一中午,等点滴打完就急急地回去了。家里实在走不开,五民的孩子让邻居给看着,中午要喂羊,要喂狗。地里的辣椒也红了,她还要乘着好价钱摘了卖掉。
牛翠莲回家后,就将大民和三民狠狠地骂了一顿。她边骂边哭,骂儿子的自私和势利。她坐在门前哭诉儿子们的不是: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你爹把你一个个拉扯大容易吗?你们只想着过自己的好日子,谁替父母想过。你爹病了,你在医院去都不去。有心哩么?狗东西们,心都瞎了。忘了谁也不能忘了爹娘老子。
刘德茂一病倒,一向要强的牛翠莲仿佛被人抽掉了脊梁骨。她一想起在医院的老伴,心里就一阵阵地发酸。她着急得坐不住,睡不着。老伴住院都三四天了,儿子们还无动于衷地去打工挣钱。她实在气愤不过,就撵到大民、三民家里大闹了一场。
刘德茂住进医院第四天,儿子大民探视他来了。大民在医院里的内科病房里挨个地找父亲。找了几个来回都没找见父亲,只好到护办室去问。当大民进来的时候,四民在给父亲剥香蕉。他一看大民手里提着的一塑料袋苹果,心里就不舒服。他接过袋子放在床头柜上。让大民坐在床边。再看看大哥,脸色黝黑,皮肤粗糙,额头上满是汗珠,身上的衣服又脏又旧。四民忘了刚才的不快,连忙给大民倒了杯水。大哥,来喝水。你先喝水,来擦一把汗。大民卑怯的神色让四民心里不落忍,又剥了根香蕉递给大民。
大民喝了水,擦了汗,才嗫嚅着问父亲:爹,你感觉咋样?要不要紧?
幸亏发现得早,要不然麻烦就大了。四民替父亲回答了。
你这两天干啥呢?刘德茂问大儿子。
辣椒红了要摘。今年的辣椒花费了那么多钱,可还是亏人了。辣椒被蚜虫腻死的多。价钱也不好。唉,今年这一年算是没指望了。一年到头白忙活了。大民长吁短叹,眉眼里蓄满了无奈和惆怅。
四民看着哥哥难怅的样子,又给递过水杯说:哥,你喝水。德茂老汉一见大儿子老师巴交的样子,将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连忙转变话头问道:园子里的苹果红了吗?大民说,没有。我和雪坠这两天在卸套袋。套袋不卸,果子不着色么。
德茂老汉一听大儿子为难的样子,就说,你忙你的。我这里你甭操心。你回吧,我不要紧。
四民看着哥哥,想起大哥要给大儿子盖房,要给二儿子娶媳妇。这两样事情没有十几万万拿不下来。再看看大哥,一脸的艰辛和疲惫,就说,大哥,你回吧。咱爹你甭操心。有我呢。
大民一听四民这话,松了一口气。连忙站起身,叮咛了几句就走了。
送走大民,四民才对父亲说,爹,你看我哥,明明知道你没牙齿,还给你拿的苹果。德茂老汉长叹了一声说,你大哥不容易呀。两个儿子每人要一院屋呢。盖一栋一层半的楼房也得花个五、六万呢。农村有两个儿子的人家都发愁呢。没有楼房,人家女娃不愿嫁么。你说,你大哥就那点本事,光能出蛮力气。如今光靠在地里刨食,难哪!父亲的话让四民哑然了。他庆幸自己考上了大学,有公家的饭碗可端。对于大哥,他深怀同情,他不管父母,那是他没能力管啊。
爹,你甭愁。我哥的事情你别伤心。只要你好好的,将病看好,身体好了,儿女们就不操心了。再说了,你还好,有我呢。有公家的工资,就饿不到你。四民说完,抓住父亲的手,紧紧地攥住了。
刘德茂刚把点滴打完,刘四民的手就响了。办公室小刘说:刘主任,局长明天要去市上开抗震救灾汇报会,要一篇汇报材料,局长叫你马上回来。接完电话,四民对父亲交代了几句,就急急地赶往民政局办公室。刘四民是单位的笔杆子,凡是领导的讲话材料、给省市的汇报材料,非得他撰写不可。这一次抗震救灾汇报材料一要把握好方向,注意分寸。他边走边盘算着材料如何下笔。等他伏身在办公桌前,就一头扎进稿子里,一心一意地写起稿子来。
刘德茂住的内科在县医院住院大楼的五楼二病室。同一病室内还住着三个七十多岁的老汉。靠窗户东边的老汉是一名退休教师。老伴日夜不离地陪护着。靠窗户西边的老汉是位退休干部,儿子在这儿守侯伺候着。他对面的老汉只有女没儿子。女儿们轮流守护着老人。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专人陪护。儿子四民一走,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点滴打完了,他坐起来,看着对面的老汉。那人的女儿一会儿剥个香蕉递给父亲,一会儿又洗了一串葡萄。葡萄粒又大又圆,看起来十分诱人。老头儿说牙不好咬不动。他的女儿就仔细地将葡萄皮剥了,露出了晶莹如翡翠的果肉来喂给他父亲。看着人家的女儿精心照顾着老头儿,德茂老汉一阵阵地眼热。自己吃苦受累将五个精壮壮的儿子拉扯大,给他们一个个娶了媳妇。他们成了家,就忘了老子和娘了。这几年,儿子们的无情无意已让他寒了心。他已经没有当年的豪迈和骄傲了。老伴是个爆性子,肚子里装不住话。她有什么事非得当面锣对面鼓说亮清不可,儿子媳妇们做了错事,惹得她一顿大骂。所以儿媳们都怯她。看着人家老汉的闺女又体贴又孝顺,他长叹一声,走出病房,蹀躞着朝厕所走去。
眼看到十二点了。四民还没有来。楼道里热闹了起来,病室里的陪护人员都出去打饭了。四民还没有来。对面老汉的女儿出去时问四民爹:要不要给他捎饭?德茂老汉回绝了。他从来不愿劳烦别人。自己站在楼梯口眼巴巴地盼着四民来。等了半天,他累得不行,就回到病床上躺下来。对面的老汉哧溜哧溜地吸面条,大口地喝汤。他吸溜面条的声音足有二尺长,他大口喝汤的声音有鸡蛋大。德茂老汉觉得那面条似乎系在自己的肠胃上,他那么一吸溜,似乎要将他肠胃从腔子里提出来。那声音周正而酣畅,让德茂老汉的两腮泛酸,不停地咽唾沫。他蒙住头,那声音象张了翅膀似的,从对面硬钻进他的被窝。他辗转反侧,难以安卧,实在忍不住了,就又走到走廊上,来到楼梯口。他扶住楼梯扶手,欲抬脚下楼,只觉得双脚发软,本来就麻木的左脚怎么也落不到台阶上,右腿也抖抖索索的,继而全身酥软,手也抖索起来。
一点钟了,有的人已经吃完饭,从电梯里走出来了。德茂老汉踅到电梯口,胆怯地看者那两扇铁门。从电梯里出来的人群将他冲向一旁。他看着电梯门一会儿合了,一会儿开了。他怎么也没有勇气踏进电梯里。第一天来时是四民搀着他进了电梯。当时,他还没有看清四民摁了哪个机关,电梯就呼地一下动起来了。一霎时,他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头晕得厉害,一下子就跌坐在电梯间。四民赶紧扶起他,紧紧抓住他的手。他无力地依靠住儿子,不一会儿,灯亮了,他又被四民牵住手,领出了电梯。当他进了病房,坐在床头时,仍然感觉天旋地转,地板好象都在摇晃,是那地震时的感觉,天在摇,地在晃。他一想起来就害怕就恶心。他看着张大了嘴巴的电梯,怎么也不敢踏进去。眼看两点了,四民还没有来,食堂恐怕早就关门了。病房里别的病人都午休了。他挪动着酸软无力的双腿,艰难地走到床边,悄悄地躺下,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响动,他又爬起来,倒了一大杯水,不管不顾地喝下去。肚子似乎被安抚住了,不再咕咕地响了。他面朝墙壁睡下了,一颗浑浊的眼泪顺着鼻梁滚进了嘴巴里。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咸咸的,涩涩的。他拉过被子蒙住头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刘四民将材料写完拿到打字室让打字员去打。打字员打完了,他又仔细地校对了一遍,出了清样拿去让局长过目。局长拿着笔这里删一下,那里添一句,犹豫不决。四民耐心地等待着,直到局长煞有介事地将材料捋码了几遍,一篇材料被局长修改得面目全非了。大概,他仍嫌材料没有体现出他的意图和水平,索性将材料扔给四民说,去,再修改一遍,我再看看。
四民看着局长那一副领导的作派,他一语不言将材料又改了几遍,才递给打字员小刘。他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才发觉肚子饿了。他让办公室小张去买了一桶方便面,等他张口吞咽时,才想起了父亲还在医院里,父亲吃了没有?他一看表,已经下午四点了,他扔下饭碗就跑出了政府大门。
德茂老汉总算是歇下了。他一歇下脑子又忙开了。他想着自己的五个儿子,他想一个,叹一声,长叹短叹引来同病房室的人的询问。他用劳作打发掉了几乎一辈子的时光,心里从来没有搁过事。当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睁大眼睛回看着身前事身后事。他叹息、惋惜、留恋。眼前的光阴短得一眨眼就过去了。大半辈子的岁月在劳累和贫穷中度过了。实指望儿子大了能享上清福。可是儿子都成家立业了,还歇不下来,日子还是个难怅。大民来了,又回去了。四民端着公家的饭碗,担着责任呢。有急事就赶紧要去办。二民生意忙,没有来。三民两口子也没闪面。五民连个电话都没打。养育了五个儿子,还不如人家一个闺女贴心。亲戚们听说了,能来的都来看望他了。他一个人的时候,就蜷缩进沉默的壳里,细数着一滴一滴往下滴的药滴。那点滴执卓而冷漠,似乎要把整个病房的寂静滴穿,又顽固地滴进人的心灵深处,一滴一滴向血液里渗,冰冷地向肌体浸润。生命似乎变得稀薄而脆弱,只是机械地一呼一吸了。
刚打了个盹,他似乎听见有人叫爹。他恍然看见五个儿子齐齐地聚在他的床头,笑嘻嘻地望着他。他心里一热,啊地一声就醒来了。他睁大了眼睛朝门口盯,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住院这六天来,他似乎每天都在等待着。这几天将他一辈子都没睡的瞌睡都睡净了。这几天似乎比他活过的七十四年还漫长难捱,那一滴一滴往下滴落的药滴比他喝过的凉水还要多。
三民终于来了。三民来时,提了一箱早餐奶。他面貌黑黢,一双大眼睛滴溜乱转,将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打量了一遍才开口问道:爹,你感觉咋样?我前几天还见你在河滩上放羊,都精神着呢么?咋会忽然之间就住了医院呢?四民打来电话说,着实下了我一大跳。
你这几天干啥着呢?
我和燕玫在镇上的建筑队干。我是大工,一天挣四十五元。燕玫是小工,挣人家三十元。刚干了几天,我妈就来说你住院了。人家这活紧得很。我今天是向老板请了半天假。爹,你不要紧么?说完,三民仔细地观察着父亲的脸色。他紧盯着父亲的脸,似乎等待父亲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不大要紧,就是头晕,恶心,脚掌发麻。医生说是脑梗塞。
四民呢?我大哥来了没有?
四民刚被单位叫走了。你大哥家里也忙。来了又走了。
爹呀,你想吃啥我给你买去。
我不吃啥。你甭买。你看你能请几天假不?德茂老汉试探着问三儿子。
这时,四民来了。四民一见三民来了,心里不由得一热。三民两口子很少过问父母的事。他今个能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今天一来,父亲的心里能舒坦些。四民赶紧剥了根香蕉,塞到三民手里,问道,三哥,你这几天忙不忙?忙么,我和你嫂子在建筑队里干活。这两个高中生一周回来一要就是五十、一百。不出去挣钱还能行?这不,刚开学两人光学费就拿走了四千块。这一周一周回来要补课费、生活费、试卷费能把人愁死。小鹏明年就要高考了,考上考不上都是个大愁帽。到时,还要你给想些办法呢。三民一脸惆怅地说。
三民的叹息让德茂老汉的心软下来了。他本想让三民陪护他几天,可是听毕他的话,他反倒替儿子发起愁来。他说,你忙就忙去吧。一天挣七八十块钱呢。他将自己的惶恐和为难藏严了,生怕儿子们担心。人活一世,哪个人不希望娃们好呢?
三民本来是来探个虚实的。被母亲牛翠莲盖头盖脑地一骂。他想来陪父亲几天让母亲消消气,结果他来一看,父亲脸色红润,似乎没有大碍。四民也在这儿,他想四民有钱又有闲,在医院照顾父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逮住了父亲的口声,便站起来说:爹,那你好好养病。我只请了半天假。我走了。
看着三民没有一点要陪护他的意思,德茂老汉的心里象猫抓似的难受。他长叹了一声。各人有各人事么,各人也有各人的难处。他要走就走吧。
四民送走三民,坐在床边安慰父亲,爹,我三哥要走,就随他去吧。他的作难日子还在后头哩。你别怕,有我哩。
三民是弟兄里最聪明的,但他往往聪明过了头。加上三民媳妇燕玫是个厉害角色。他们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根本就把老人没搁在眼里。当时,四民打电话给三民的时候,三民就说,让五民回来,爹妈跟的是五民,又替五民看孩子。爹病了,五民理应回来照看。
四民将这些话藏在心里没敢给父亲透漏。五民两口在广东打工,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不是还有四个儿子在跟前吗?四民就盼望着二民回来,能替自己看护几天。他自己当老板,不受人约束。他赶紧在楼道里给二民打电话。二民在电话里直嚷:啥?大民、三民都在家,不出钱还不出力,回去要开家庭会议,要将责任分割清楚!
四民说:哥,爹病着呢么。开啥家庭会议。儿子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要有一份孝心就行了,何必搞那么复杂。让父母难怅?
二民说,对呀。咱出了钱还要出力。正因为这才要开个会把责任和义务掰扯清楚嘛。
四民说,开会的事以后再议。我爹也是你爹,你不回来看看。你也不对。
二民一听四民的话音不对,又转过弯说,要花多少钱你言语,我给你打过来。
四民说,我不要你的钱,你有孝心,就自己缴到医院吧
德茂老汉住进医院的第八天,二儿子二民开着本田车回来了。他一进病房,就抓住父亲的手问,爹,你不要紧吧?医生咋说的?能不能治彻底?我去给医院说,让他们用最好的药。他那大款的做派让同病室的人都刮目相看了。四民一看,放心了,就去上班了。
二民给医院缴了两千元,又为父亲买来了面包和蛋糕等好吃的东西。他的手机不停地响着,都是生意上的事。二民人在医院里,心却牵挂着他的生意。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水果批发市场进来了大量的香蕉、柑橘和葡萄,业务量大得二民媳妇应付不了。她不停地给二民打电话讨主意。一瓶针剂没有挂完,二民就接了十几个电话。《两只蝴蝶》的歌声不停地在病房里响起。那歌声粗糙而直接,渐渐地变得聒噪起来,后来竟成肆虐了。二民频繁地去走廊上接电话。他的声音里透着焦急和无奈。他接完电话,又看看憔悴的父亲:衰败无力地躺在病床上,稀疏的白发,一张饱经沧桑的脸,额头上密匝匝的皱纹,两颊塌陷,目光呆滞而无神。父亲强壮如牛的岁月已象轻俏的风一样随着记忆渐离溅远了。他不由得鼻子发酸,走过去,紧握住了父亲的手。随后,他狠心关掉了手机,病房里恢复了往日的静谧和细腻。老人们都扯起了短促的鼾声。
有二民在医院里,四民也就放宽了心。他被琐碎的日常事物纠缠住不放了。
二民在医院里陪护了三天,二民媳妇周玉萍就急匆匆的从省城赶来了。二民几天不开机,她的心越发毛躁。快中秋了,批发市场上的生意十分火暴,她一个人根本就应付不过来。她不知道公公的病到底怎么了。她心急火燎地搭车回来,一进病房,却见二民靠着父亲的窗头打盹。她恨不得抓二民几把。自己忙得提起裤子寻不见腰,他却躲在这里睡大觉。她从热火朝天地场面中艰难地拔出来,一下子跌进棉花团一般的宁静与安闲之中,就象烧红的铁块在一盆凉水中淬火一样,伴随着“滋”的一声,水中冒出了一股蓝烟。周玉萍抓住二民的衣服,将二民拽到楼道里,气急败坏地要打架。
德茂老汉醒老了,他向门口一瞄,便瞅见二媳妇的饿影子。不知他们两个人在唧咕着什么?德茂老汉的心里不由得一阵发紧。他平时不轻易和儿媳着嘴。在他的意识里,媳妇们是外人,也是女人,毕竟监视短、眼光浅。他从来就不正眼看媳妇一眼。这似乎让他显得和威严。
二民和周玉萍说地声音大了,似乎在争吵什么?他不仅抬起身子小,想听明白他们到底吵架了没有。他埋怨自己,怎么就老糊涂了呢?怎么连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自己耽搁了儿子的生意,使他们良人争嘴。等二民和媳妇进了病房。他从周玉萍的眼神中读出了复杂的东西。周玉萍见公公醒来了,忙打扮了一张笑脸,笑眯眯地问道,爹,你感觉咋样?医生没说还得几天出院?
德茂老汉看看儿西服,又睃了一眼儿子,他知趣地说,不要紧,好多了。这几天生意咋样 ?周玉萍说,哎呀,把人能忙死。在节前要把香蕉和葡萄全发出去。抢个好价钱。二民看看媳妇又看看父亲,一个劲挠头。他在脚地转圈子,转了几个圈子,又走到走廊上踱步。刘德茂老汉见儿子受煎熬,就忍不住了。他对二媳妇周玉萍说,你们生意忙,就让二民走。我这里能行。去把二民叫来。二民近来说,爹,要不我在陪护几天?德茂老汉挥了挥手,说,走吧。我能行。你给四民打电话说一说。你谅可以走了。
二民一走,四民又恢复了中午陪护,下午上班。眼看中秋节到了,单位里忙着采购月饼和水果等慰问品。医院里能个回去的人都纷纷回去了。四民又去问了主治大夫。大夫说,你父亲这病,来地慢去地也慢。脑子里有四处梗塞,手脚麻木和颤抖的症状一时半会环节不了。现在主要是软化血管,防止去他血管堵塞。这是个缓慢的过程,起码得三个疗程,三周时间都不行。四民一看,想赶在中秋节前让父亲出院看来是不行的。他只好耐下性子,坐在床边,看者点滴一滴一滴地往下滴。
中秋节这一天,郝彩虹和刘早也来到医院。刘早将月饼塞进爷爷手里,自己偎在爷爷身边玩耍。中午,两瓶吊针打完了,四民和媳妇掺着父亲上了电梯,走出医院。街道上人来人往。大人,孩子,男人,女人,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
德茂老汉被儿子四民产妇着走在人行道上。刘早欢快地在前面蹦跳。逛悠了几十米远,他的手心冒汗,两腿发飘,头脑晕晕忽忽的。他让四民慢点走。孙子刘早在前面跑一阵,停下来叫爷爷。后来,他实在走不动了,就一屁股坐在台阶上,长长地喘气。他看着来来往往的一只只鞋。皮鞋、运动鞋、步鞋在街道上匆忙或悠闲地点动。那清亮、软遢的声音就象麦苗一样旺在了街道上。脚步所到之处,喜悦喜庆喜气被播种了一街道。
德茂老汉的脚步太轻飘太脆弱,跟随着孙子欢快的脚步,儿子矫健地脚步、媳妇轻捷的脚步从东大街漫到南大街,走到一家饭店门口,他又一次坐下来再也不想站起来了。四民恍然记起了父亲是个病人,他愧疚地说,爹,累了吧。咱吃饭。就在这家饭店吃。
饭店里人挤人,到处充斥着密匝匝的饭食的味道。好不容易等到了饭菜,德茂老汉已经饿得撑不住了。他端起白饭就往嘴里刨。
吃过饭,四民叫父亲跟他们一起回家。他的家在东关小区,来回要坐车。德茂老汉累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他连一寸路都不愿意走了。他烦躁地打发走了四民一家,就一步一步踅进医院,抓住扶手向五楼爬去。
等他睡了一觉醒来,偌大的病房就剩下他一贯人。月亮从东边楼顶徐徐升起,露出又红又圆的脸蛋。月亮升起来之后,静静地悬浮在医院的玻璃窗外。月光把病房照得象清水洗濯过一般澄澈透明,整个房间就像泛在湖面上的小周。月光下,铁管床,白色的单子和被子,奶油色的柜子,冷峻的白色瓷砖,一切物品象被镀上了一层因粉。床与床之间的距离显得遥远而不真实。月光似乎照上了他的额头,他仿佛看见了月亮上班驳的影子。
看者轻纱般的云翳披拂在月亮清冷的精身子上,德茂老汉不觉一阵发冷。无法承受,无法稀释的忧郁与寂寞象迷雾一般从心底弥漫开来。意义、无助象潮水一样汹涌地袭来。他金笔双眼,紧紧抓住薄薄的被头,那泛滥的潮水盖头盖脑地袭击了他之后,又消失地干干净净。他坐起来,再也不想在病房里呆一秒钟。他站起来,看着窗外,也不忍去看月亮饱满的身子,冷峻的面容。清辉漾在物什上,看上去就象蒙上了薄薄的尘埃。他似乎看奖了自己,如日中天、气壮如牛的自己和灿烂如花、妩媚多情的老伴。自己身后,五个生龙活虎的儿子。渐渐的,自己干枯了,老伴的笑容消失了,只剩下了虚弱委琐的外壳。他的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岁月留下的苍白痕迹看上去是那么虚无飘渺。这一刻,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寒冷和软弱。
他站起来,蹒跚着向门外走去,脚步踉踉跄跄、歪歪扭扭。那种孤独感太瘦弱了,瘦而尖锐,划破了他衰老患病的肉体。楼道里空空荡荡的。空荡荡的空间变得烟雾弥漫。他似乎被浓重的烟雾笼罩住了,任他怎么挣扎也挣不出诡异粘稠的迷雾。他几乎崩溃了。周围的一切静默无语,他似乎走进了一座死城。只有电梯张大了硕大无朋的嘴巴,等待着他。电梯里寂静无声,危机四伏。
他的双脚绵软无力。当他迈进那间铁屋子之后,一股热浪袭上了胸部和头部。他站立不稳,扑倒在电梯里。
【免责声明:本站所发表的文章,较少部分来源于各相关媒体或者网络,内容仅供参阅,与本站立场无关。如有不符合事实,或影响到您利益的文章,请及时告知,本站立即删除。谢谢监督。】
发表评论
推荐资讯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