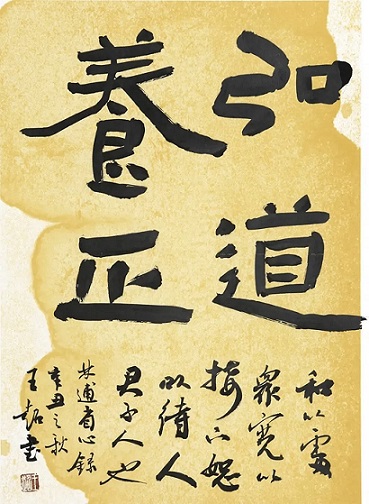很早就想写一点关于母亲的文字,只因歌颂母亲的文章实在太多,而自己的母亲又着实普通,一如天下大多数慈爱的母亲,故而迟迟未有下笔。父亲过世后,母亲跟我一起生活,时间一久,对母亲有了更深的理解。忽地觉得,作为一个儿子,过去其实并不完全懂得母亲。
母亲,一位平凡的女性,却有许多不平凡的事,值得一书。
1
井冈山下的莲花县花塘乡,有一个叫“漫坊”的小村。1929年冬天,母亲出生在这个小村的一户刘姓贫苦农民家庭,排行第四,取名“冬娇”。那时,正是国内土地革命最为残酷的年代。莲花,这个小县恰处于红、白势力轮流割据的地方。
母亲的生父,也就是我的亲外公,姓刘,叫什么名字我记不住,母亲也只是简单说过外公的事。外公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赤卫队,因说话直率,被红军当作“AB团”成员误杀。当时,错杀的人很多。这是红军苏区时期的一大悲剧。解放后,人民政府给外公平了反,定为烈士。母亲说,井冈山烈士纪念碑上刻有外公的名字。母亲的生母姓樊,名叫冬英,是一个身材高大、性格刚烈的苦命女人。
旧社会,失去了丈夫的女人是很艰难的。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寡妇,最有能耐也难以抚养四个幼小的儿女。无奈之下,外婆把大姨送给了一户穷人家做童养媳。年仅两岁的母亲,被送去给本县下坊乡汤度村的一户贫苦人家做干女。二姨在冬天烤火取暖时,不幸烧伤,无钱治疗夭折。四个小孩,外婆只留下学理发手艺的大儿子——舅舅在身边,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母亲的养父姓贺,也是一个苦命的本份人。继外婆没有生育子女,她把母亲当着自己的亲生女儿。母亲的名字便由“刘冬娇”改为“贺小莲”。不久,母亲的养父因病去世,母亲的继母,迫于养家的艰难,招赘入门了一个弹棉花的手艺人,也没有生育子女,又领养了一个穷人的小男孩做养子。就这样,没有血缘关系的四个人组成一个家,艰难度日。
这些,都是我帮母亲填写履历表时才知道的。
母亲和其他的老人不一样,平时很少唠叨,也不常回忆儿时经历的苦难。偶尔一次,我好奇地问起母亲小时的事,母亲提起一次她跟邻居的成年人去吉安城贩卖鱼干的经历,伤心不已。
外婆为生计所迫,劝跟老乡去吉安,做点贩卖鱼干的小生意,懂事的母亲跟着去了。那年,母亲年仅十二岁。
解放前,莲花至吉安一百多公里的路,坎坷难行,狼叫狗吠,常有土匪出没。一个小姑娘跟在成年人的后面,风餐露宿,昼夜兼程,来回走了三天两夜。多亏邻居关照,往返三天三夜,总算没有掉队。回家后,母亲脚下的布鞋磨出两个洞眼,脚底胀满了黑血泡,挪一步肉如针扎。母亲赚来的几个浸透了汗水的银毫子,路上一分也舍不得花,一五一十地交给外婆。外婆噙泪数钱,母亲泣不成声……故事未有说完,母亲几声长叹,老泪盈眶。
从此,不再多问母亲苦难的往事。伤心痛楚的记忆应由母亲独自尘封,或许这也是做儿子应尽的孝道。
2
“千年铁树开了花,万年的枯木发了芽”。1949年8月初,解放军洪流般南下,随军工作队派驻在莲花县的每一个村庄。工作队的到来改变了农村妇女的命运,也改变了母亲人生方向。在乡亲们的举荐下,母亲被南下工作队的一位女领导看中,担任了村妇女主任。不识一个字的母亲,凭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激情,发动群众支前,工作干得十分出色,很快成为组织培养的好苗子。
十九岁的母亲,宛如一朵长夜里煎熬的莲花,终于迎来拂晓的一刻。
次年,母亲正式填表参加革命工作,改名为“贺哓莲”。不久,加入党组织,选派去了吉安地区的基层妇女干部学习班,进行政治和文化的启蒙。从家里珍藏的一张的旧照片上,依稀可见母亲当年的风采。身着束腰的列宁装,衣袋别着的两枝钢笔和校徽一样的小牌,脸上露出灿烂的笑。之后,母亲担任一个区的妇联主任兼区辖乡的乡长。
此时,外婆以母亲为荣,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寡妇得到了村里人的尊敬。
母亲说,刚参加革命工作时,外婆是横直不同意的。外婆胆小,忌讳阶级报复,怕受牵连,不想让一个姑娘家走家串户,四处忙碌,去做动员群众斗争地主的工作。还有一个原因,外婆辛苦十几年把母亲拉扯大,希望母亲和其他农村女孩一样嫁人,生儿育女,可以收回一些聘礼。一下子被组织要走,好象是自家田里熟了的稻子被别人抢割了去,心里顿觉失落。
母亲说,那个改变她人生命运的女领导是县第一任妇联主任,姓郑,一位南下干部,时任县委第一书记的爱人。当时,外婆对母亲好言劝阻没有作用,采取了夜晚栓门,不留饭菜的做法刁难母亲。母亲夜晚开完会归来,半晌进不了家门。软泡硬磨进了家门,又没了饭吃,饿着肚子睡觉,次日无力工作。郑主任知道后,要母亲带路,来到外婆家,说了一番大道理,外婆的思想疙瘩无法通窍。郑主任拔出腰间的小手枪拍在外婆家的饭桌上,铁着脸“骂”外婆阻碍革命,要通讯员要把她抓起来。“恐吓”的方法管用,吓得外婆哆嗦,哭了起来,保证再也不阻碍母亲的选择……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母亲特别内疚而又深感幸运。
母亲说,养母是个老实守旧的农村妇女,哪里见过这个场面。倘若领导不是这样恐吓,外婆很难答应。倘若母亲不是幸运地遇到那位姓郑的主任,命运将是重复一个农村养女的悲哀。
3
参加革命后,母亲迎来了新的生活。
母亲自由恋爱,嫁给了一位英俊、有文化、有个性,却缺乏仕途应变能力的热血青年——我的父亲。父亲是建国初期参加革命最早,提拔最快的青年之一。但父亲正直的品性,刚烈的脾气,给自己带来了人生的灾难,也给母亲带来了刻骨铭心的痛楚。
母亲和父亲结婚后,一起选调到地区工作。父亲在地委组织部门任正科级组织员,母亲在农业银行当副科长。上司都是那些或长征或南下的老干部。反右运动开始,父亲的耿直引起了个别领导的不满,好在父亲的作风过硬,家里三代都没有污点,主要领导没有画圈,才逃过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一劫。
很快,组织通知父亲下放,去当年彭德怀、黄公略打游击的吉安县东固山拓荒,担任了东山垦殖场一个分场的场长。母亲随行,安排在另一个分场劳动。
东固山,现在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当时的东固山,却是一片荒凉的虎豹豺狼经常出没的原始森林。
在垦殖场的日子里,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孩的母亲和父亲一样,年年都是总场的劳动模范。白天,母亲和男同志一道拓荒造林。晚上,母亲要照顾两个嗷嗷待哺的小女。当时的生活条件是那样的艰难,母亲肩负着一般的妇女承受不了的担子。不久,母亲遭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母亲因疲劳酣睡,两个女孩捂死在被子里都没有察觉。母亲含着泪水和父亲一起,在劳动的土地上挖了个深坑,掩埋了自己身上掉下的两块亲骨肉,继续投入火热的建设。
这段难忘的岁月,酷似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翁保尔抢修铁路的那一章描写的情景,共产党员以信念为支撑,任何工作都发挥了榜样的作用。拓荒建设中率先垂模,以苦为荣,毫无怨言。
母亲说,她也有过骄傲的回忆。偶然的机会,吉安县的主要领导,也是父母参加工作时候的老领导,知道父母的情况后,又把父亲调入县委监委工作,母亲则分配在一个区里任区委委员兼妇女主任。这时的母亲有过一次幸福的经历。196年3月的一个日子,朱德委员长携带夫人康克清回到井冈山。作为县里唯一的基层妇女代表,母亲有幸参加了接见。据母亲回忆,当时规定参加接见的人不准主动和中央首长握手,不准随便说话,只能站立鼓掌。不料,朱委员长突然向母亲提问:你们领导对妇女工作重视吗?母亲由衷回答:领导十分重视我们妇女工作。朱委员长很高兴地说:“哦,你们的领导做的好。”……
母亲违反了纪律,却得到了县委主要领导的表扬。这是母亲最难忘却的记忆,母亲的记忆只是留在心里,很少和别人聊起,更没有写下点滴文字来标榜自己。
后来,母亲又生养下我和姐弟四个孩子。家庭经济十分拮据,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母亲的身体终于垮了,想回老家有个照应。经组织的同意,父母调回老家的县委工作。父亲在县委搞党务工作,母亲先后担任城镇党委副书记、县委机关保育院院长、县政府人民饭店经理,飘泊的日子总算安宁下来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时隔不久,“文革”运动爆发,大陆开始了强权政治的时代。
父亲又因耿直得罪了那位一手遮天的县委主要领导,全家被迫流放到更为偏僻的山村,母亲担任村里的支部书记。1969年,黑色的年份。一道“莫须有”的罪名将父亲关入了牢房,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最初连母亲都不知道丈夫已进了监狱。来逮捕父亲的人,说是通知父亲去县城开会。后来,听说父亲被人举报参加过“大陆反共救国军”,并是一个子无虚有的“88司令部”司令。母亲说父亲建国前就一心跟随着共产党干革命,如何竟成反革命呢?联想到自己生父在大革命时代的错杀,深深为父亲的安危担忧。现在看来近乎荒唐至极的事,在过去的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却可能发生。
往后的日子愈发艰难。仅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五个小孩。白天,母亲要和农民们一道下田耕作;晚上,母亲要参加公社无休止的政治学习会。除了娘家亲人,其他的亲戚和昔时的同事都不敢登门。
月明星稀,乌鸦鸣叫。劳作夜归的母亲望着熟睡的五个未成年的子女,不知暗地流下了多少伤心的泪水。有人劝母亲改嫁,说父亲是永远翻不了身的。母亲没有啃声,带着大的只十三岁、小的只一岁半的五个子女,艰难生存。默默的期盼着光明的到来,没有向任何人低下过倔强的头颅。
那时,我已有五岁,记忆的深处留下了痛苦和受辱的烙印。
几经搬迁的家,定格在一个老乡闲置的旧房子里。潮湿不平的黑泥地面,柴火熏得乌黑的楼顶,报纸糊着的窗户,一家人躬身于此,躲避暴风淫雨。
一个漆黑的夏夜,母亲的手无意触摸到一处冰凉,惊醒过来,发现是一条一米多长的蟒蛇,同眠枕边。怕它伤害熟睡的子女,母亲抄起床边防身的木棍将蛇打死。过后,房东大妈对母亲说,蛇是家里的保护神,是只能赶走不能打死的,打死会有灾难的。素来不信鬼的母亲,竟吓得上街买来冥纸烧香陪罪。可见,母亲此时的心理,已脆弱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个寒冷的晨冬,家里的门窗紧闭,房里弥漫的浓厚煤气。昏迷中,母亲意识到是煤气中毒,却无力动弹。极力呼唤睡在门边的二姐打开木门透气。二姐微弱回应:“妈,我也全身乏力。”母亲说:“孩子,你要用力开门呀!不然就要熏死全家”。懂事的二姐艰难地爬了过去,终于把木门打开。冰冷而清新的空气把瘫在地上的一家人刺醒。全家得救了,母亲和我们抱成一团哭泣。
母亲太累了,承担不了五个子女的重压。又有好心人上门,劝母亲应把只有一岁半的妹妹送给别人,母亲痛苦地答应。没有和谁商量,也没有人可以商量。天黑夜沉,母亲哭了,怎能让女儿又重复自己的命运呢?清晨,母亲反悔了,死活不兑现昨天许下的承诺。妹妹终于还是没有送人。
隐约记得,母亲带着哥哥和我去过一次县公安局的监狱,给狱中的父亲送寒衣。楼道上,一个持枪哨兵在游荡,威严的眼光,令人不寒而栗。母亲在哀声托人说情,兄弟俩在操场上等候父亲的出现。那时,我并不知道父亲呆在里面干什么,也不知道为何在这里见父亲。父子见面,兄弟俩也只是按着母亲路上来时的叮咛,麻木地唤声“爸爸”。而今想来,那时的母亲承受的压力是多么沉重。
八个月后,外来的解放军代表接管了父亲案子,打成反革命的父亲终于出狱。清楚记得,那晚全家团圆的情景。桌上摆满了好菜,有一大钵的红烧肉。哥和我夹了菜端碗在外面吃饭,哥把一块大肥肉扔到菜园里,我急忙进屋向母亲告状,却见母亲坐在父亲身边,只是宽容地笑。尚小的我不懂,平时严格的母亲为何如此宽容。
“文革”过去了许久,家中每一个樟木箱的铜扣上仍留有被抄家时撬锁的印痕。我想,母亲的心灵深处肯定也存有磨灭不掉的伤痛。
5
持续十年的“文革”动乱结束后,母亲的伤痕渐渐平复了,过上了安详的生活。
母亲胸怀宽广,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家迁回县城后,邻里邻舍相处和睦。一些过去见了母亲唯恐避之不及的乡下亲戚,时常来家中蹭饭。母亲一如从前,热情接待,无丝毫埋怨或怠慢。见子女有些埋怨,母亲说:“不管过去如何,总是亲戚的,来了要接待。”与朋友交往更是如此。有一户邻居是父亲的部下,在“文革”期间做过一些“落井下石”的事。父亲心存芥蒂,不愿意与之来往,母亲闭口不提过去的是是非非,好象把那些痛苦忘却干净。这户邻居的儿子结婚,没有场所地举办仪式,母亲主动联系单位的会议室,帮助着操办,热情真诚,相处很好。
母亲非常勤劳,从小教我热爱劳动。早晚的时间,母亲带将公房后面的几分园土打理得平平整整,象一页书。栽上冬瓜、茄子、豆角、白菜,一年四季,菜蔬不断。母亲还把大门的走廊格成猪栏,养猪养鸡,聊补生计。放学后,兄弟姐妹一起跟着母亲整土、插苗、施肥、剪枝、收获,帮着母亲剁猪草、煮食、喂猪……掌握了一个农村娃应懂的农活。
母亲心地善良,对弱者充满爱心。有家邻居,小孩较多,饭吃不饱,母亲知道后要我把收获的一个十几斤重的大冬瓜送去,解决了邻居几日菜肴。还有一户人家,他要母亲帮忙办事,中秋节前送来一只鸭子和一篮鸡蛋,放在家门口。母亲了解后,连夜把东西送了回去。怕原物送还引起误会,还另加上两封芝麻饼。母亲对那人说:“你家很困难,不能收你的东西。该办的事一定会办好。”那户人家感动得流泪,不停地言谢母亲的好。
相伴十几年的邻里街坊,没有谁不被母亲的善良、热情所感动。时至今日,那些老邻居,还经常叨念着母亲的好。母亲说,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
确是如此。八十年代初,政府允许干部建私房。家中子女都长大成人了,两间公房实难容七口之家。母亲思虑着为子女筑个自己永久的“巢”,免得四处搬迁。当时,父母一辈子的积蓄只有200多元,仅够买几根木料的钱。邻居知道后纷纷主动借钱给母亲。有户吉安县的老熟人,特地从百里之外送来200元现金。对于借款。母亲一一登记,和子女一道订立还款计划。就这样,母亲东借西凑了一万多元钱,买起了砖瓦等材料。父亲早晚劳作,亲朋好友大家出工,在一个荒坡上,终于搭起来了一栋自有的房子,结束了二十多年“无家”的流浪生活。
几年后,子女五人都有了幸福的小家庭,剩下父母两老固守着老屋,等待一年一次的春节团聚。一九九五的重阳节,父亲去世。母亲跟着子女轮流生活,把家中的什物送给生活可怜的人,说房子也不管了。哥哥提出将房子处理,我没有同意。让母亲生前看到自己的老屋,换成一叠不带情感的钞票,实在有些不忍心。
而今老屋依在,借给了没有房住的人家。母亲说:“老屋不卖还是很好。大半生借别人的屋住,现在借屋给别人住,也算是一种回报吧”。
6
母亲老了,乌黑的头发变得斑白,远远看去象沾了一头冬霜,双眼也失去了昔日的乌亮,患有白内障的双目有点浑浊,骨子增生扭弯了母亲的腰板,高高的身躯矮了许多,脚肚上隆起的动脉象爬满了蚯蚓……沧桑的岁月给她留下了劳累过多的痕迹。
晚年的母亲,心如无波的老井,显得豁达,宁静,淡泊。
七十年代末,政府对历史遗留的问题,大多了落实政策。由于种种原因,母亲的政治待遇始终没有得到落实。我几次带着母亲的材料,去找过老家的县委领导。那些年轻领导礼貌而圆滑地答复:“非常理解你的心情,过去的事很难办,要慢慢来。”说白了,就是新官不理旧事。当时,我有些气愤。母亲知道后,平和地劝道:“不要再提此事。我已是快要入土的人了,何必自寻烦恼。况且,和那些一起长大的姐妹相比,已经够幸福了!”
母亲的话,使我的心情释然,心中不平的垒块随风消去,对世事有些大彻大悟了。是啊,人在世界上走一趟很不容易,总有许多的事不遂人愿,要懂得知足,学会感恩,保持快乐。母亲今年满八十岁,身体依然健康,心情依然快乐,已是儿女最大的幸福了,其它的事情微不足道了。
7
我的文字实在太嫩,难以详细地记录母亲一生的坎坷,难以生动地刻画母亲意志的坚强,难以淋漓尽致地表达我的对母亲的敬爱之情。母亲的一生,诠释了一代中国女性苦难的深度与承重的力度。解读母亲的一生,我有了面对人生曲折的信心和力量!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