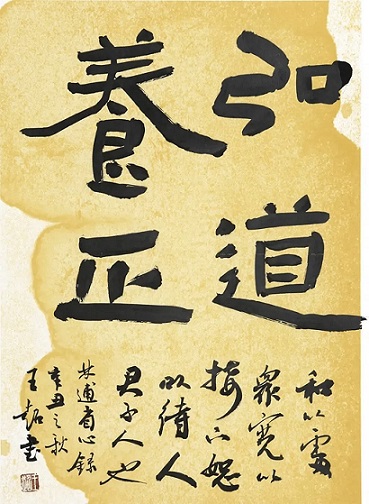1979年我第一次离开故乡昆明,受李白的影响,自觉书已经读得差不多了,要顺江东下,云游名山大川。最后去到哪里呢?李白去了长安。那时候中国没有长安,北京是政治中心,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像古代长安那样,诗人云集。或者三十年代的上海,一块砖头砸过去,必然砸到文人骚客的脑袋。那时代最匮乏的东西不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太强大了,就是在工厂里的工人,马克思的资本论选段也是要学得个唰唰纸响。工厂每年都要搞多次政治学习考试,那论述题是什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还要结合实际,不是死记硬背就完事的。工人在一起开口闭口都是唯心唯物这些抽象概念,不一定像哲学专家那样明白究竟,但是哲学名词已经成为口语的一部分。最匮乏的东西是物质,当时我还没有考进大学。还在一家工厂工作,以现在的时装标准衡量,我们那时候的形象就是一群破衣烂裳的流浪汉。上海是一个物质中心,上海产,那就是最好的,昆明人以家里拥有的上海货多为荣。长江的终点在上海,我于是来到了上海,那一年我25岁。
夏天,我站在南京路上望着那些摩天大厦,心中荡漾着的是青年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我刚刚读完了斯汤达的《红与黑》,于连是我的偶像,我想象中的于连就是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我们在人民公园附近的一家冷饮店里喝了咖啡,很难喝,但在上海喝咖啡这是我从三十年代小说里得到的印象。后来我们决定去一家饭店里豪华地吃一顿,像那些十里洋场的中产阶级。我们走进摩天大楼中的一座,平生第一次穿过旋转门,餐厅里坐着全是穿中山装的人,像是正在开会。我跟着侍应生走到其中一张餐桌坐下,菜单就压在玻璃板下面。我瞟了一眼,站起来就跑。那菜单上,最便宜的菜是13元人民币。吃不起也不至于跑吧?那时候我老害怕着被逮捕,你进入任何一个地方人们都很警惕,戴红袖套的人到处都是,要盘问,要检查工作证。在上海的胡同里,人们已经不习惯陌生人出现,我们偶尔穿过,正在闲聊的老太太就一齐停下,盯着,看你要干什么,然后窃窃私语半天。你走进了一家大饭店,100万人只有那么几百个人敢于走进去的大饭店,你坐了下来,却什么也吃不起,这不是很可疑吗?所以我们拔腿就跑,在饭店里的服务员警觉起来之前。幸好没有人出来追我们。一直跑到南京路上,哈哈大笑。我们每个人身上只带着100多元人民币,晚上住在火车上,白天旅游。实在不行要住旅馆,也是去住大众浴室。晚上浴室不营业,供浴客休息的床就出租,五毛钱一个床位,还可以洗一澡。只是床是坡形的,躺一下很舒服,长睡就太难受了,但我们总是睡得很香。南京路上人群密密麻麻,都是来买上海货的,但商品并没有堆积如山,商店并不多,少数的几家店里,挤得水泄不通,也就为了秤几斤大白兔奶糖带回去。我们中的一位,第一次出远门,怀里揣着一百元人民币的巨款,缝在内裤上,感觉到处都是小偷,他自告奋勇,总是跟在大家后面,提醒我们这个人很可疑,那个人眼神不对,小心啊,丢了就回不去了。我在一家较小的铺子里买了一双黄皮鞋,22元,这种皮鞋我在红卫兵抄家的时候看到过一双,但昆明的皮鞋店里的皮鞋都是黑色或棕色的。除了这双皮鞋,我还买了两本书,就是我此行的收获。晚上,我们去外滩看,外滩在中国相当有名,就像一个传说中的诺亚方舟,名声暧昧,与男女之事有关。去过的人神秘地说,你去了就知道了。而且告诉我们要在八点到十点之间,去早了,人还没有来,去晚了,人就走了,戴红色袖套的人不准大家呆到十点以后。我们到了外滩,看呆了,一对对男女面贴面,搂着、抱着、挨着、一对接一对,沿着黄埔江边的栏杆排下去,一眼望不到尽头。就像解放前夕,钞票贬值,南京路上排队换金圆券的人,只是排队的目的不同。大家耳鬓厮磨,喁喁私语,嗡嗡之声像是天空里飞翔着无数的蜜蜂。那个时代这个国家到处是高音喇叭,你在公共场所听见大些的喧哗,那必定是在喊口号、念社论、开庆功会、批判会。公众,居然发出这种声音,我从来没听过,将来恐怕也不会听到第二次。有些人居然抱成一团!没有路灯,黄浦江上有些微弱的光,只看见黑影憧憧,也够令人热血沸腾的啦。在外省,这可能就要被当做流氓抓起来。新来的恋爱者,只有在一旁等着,等先来的恋人谈完走了,才能插进去。我们走了一阵,看别人谈恋爱,很是孤独。
上海我太熟悉了。我当时工作的工厂,就是从上海搬过去的,厂里的师傅大部分是上海人。我初中没有毕业,就被国家分到工厂去做工,我的师傅就是上海人。外号排骨,因为他相当瘦。说是师傅,其实他只上过小学,家住在闸北区。国家号召支边,支边就可以有个铁饭碗,18岁就跟着工厂来到云南,我们的工厂,就是这些上海人在一片坟地上盖起来,然后运来机器,生产产品。我来到这个工厂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上千人的大工厂了。我师傅看不来图纸,交给我们干的活计,还得我看图纸,开始他偶尔支使我去给他买烟,后来知道我比他有知识,很尊重我,我们相处得很好。他经常给我说上海,说十里洋场、说百乐门,说城隍庙、说小K,上海给我的印象,是个很好玩的地方。我看过王重义的连环画《十里洋场斗敌记》,怎么斗的我忘记了,只想着将来要去上海玩玩。工人们也说北京,但我从来没想到北京去玩,我想的是去北京瞻仰瞻仰天安门故宫什么的。我们生产的产品是矿山运矿石的翻斗车,每到月底,就把刚刚漆了黑油漆的矿斗,一台台垒到大卡车上运走。那是一个欢乐的时刻,全厂一起出动来干这个活,男女工人一边推矿车,一边彼此打闹,就像在秋天乡村的打谷场上。上海人不喜欢空谈,空谈是那个时代的普遍风气,就是一个普通工人,也是心怀全球,想着怎么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像是游击队的政委。上海人大部分不喜欢高谈阔论,技术很好,工作一丝不苟,勤俭,干净,钻头觅缝地过小日子。我记得有个车工,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给邻居缝补衣服,他裁剪,老婆缝,缝纫机整晚哗啦响。那老婆,长得白,很美,每天要拿个箩筐,到大路上去捡煤渣。她知道那些运煤炭的大卡车几点会从工厂门口经过,工厂门口有些大坑,卡车一过就要颠下些煤炭来。车一走过,工厂里的女人就上去抢。有一天,这个女子,被卡车撞死了,尸体抬到大路边上,脸和手很白。他正在车间里车轮子,听到噩耗,戴着手套就跑,哭得个呼天抢地,风云变色。他们夫妻,感情很深。我1980年考上大学,就离开了工厂。二十年后我偶然回去,这个工厂已经倒闭,荒草丛生,厂门口挂着条大标语,要求解决职工的养老待遇,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工人在标语下面坐着发呆,我没有看见我师傅在里面,他已经老得不能出门了。
热衷于过小日子,在我们时代,是要被鄙视的。我经常听到人们揶揄某人,就说他只会过小日子。过小日子,那就是小市民。谁不是小市民呢?大市民又是谁?好像19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没有鄙夷小市民的传统,市民就是市民,无所谓大小,没有贬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市民社会的颂歌。西方的看法不同,恩格斯揶揄他民族最伟大的诗人歌德是法兰克福的小市民,“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主张歌颂叱咤风云的无产者,反对歌颂小市民的鄙俗风气。这种思想影响了十九世纪以降的世界激进文学,成为时髦。写日常生活的上海作家张爱玲,被许多大文豪视为庸俗。她居然写这些:“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 烧鸭煨汤,汤清而鲜美。烧鸭很小,也不知道是乳鸭还是烧烤过程中缩小的,赭黄的邹皮上毛孔放大了,一粒粒鸡皮疙瘩突出,成为小方块画案。这皮尤其好吃,整个是个洗尽油脂,消瘦净化的烤鸭。” 鲁迅当年也住在上海,他住在四川北路。读鲁迅的文章,你看不出这是一条怎样的四川北路。今年我又去了上海,到了四川北路,发现那就是过日子的好地方。在一里弄里,我吃到了上好的老鸭粉丝汤,真是美味之至。鲁迅大约对老鸭粉丝汤之类的视而不见,他的文章里从来没有提到,他吃不吃呢?不知道。我想起甘地,奈保尔说,尽管甘地在英国待了三年,他的自传里却丝毫未提及气候或季节,除了到达当天正值9月末,甘地穿着白色法兰绒登岸,因为不适宜而感到尴尬,下一次明确提到的时间,是他离开那天。“没有关于伦敦建筑的描述,没有街道,没有房屋,没有人群,没有公共交通。1890年的伦敦是世界之都,对一个来自印度小镇的年轻人来说,伦敦一定叹为观止”。奈保尔认为甘地“精神内聚是强烈的,自我专注很完整”。“他的体验,发现和誓言,只满足着他自己作为印度教徒的需要,满足在置身敌意中界定并强化自我的需要,它们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奈保尔肯定是这个世界普遍的小市民中的一个,他关心的是生活世界的在场,是日子如何过。他大约会同意张爱玲女士的名言“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20世纪,文豪关心的是“中国向何处去”,宏大叙事成为时代写作的主潮。到文革时代,过小日子都已经成为罪行,“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成为革命的对象。革命不是绘画绣花、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暴力成了生活的常态。都热衷于过大日子,大日子怎么过,在广场上,服装一致、万众一心、旗帜招展,高音喇叭。恩格斯的观点只是他的观点而已,并没有使德国成为鄙夷小市民的社会,托马斯·曼、卡夫卡、伯尔……这样的小市民作家继续出现并伟大。而在中国,鄙夷小市民却成了人们普遍的价值观,真是可叹!二十世纪,人们为主义、观念而活,不为过日子而活。但日子总得过,过日子事关吃喝拉撒,文化上不给这些事情正名,于是小日子总是过得偷偷摸摸、猥琐狼狈。如果不是美国的一位文学批评权威夏志清出来赞美张爱玲,我很怀疑中国读书界是否会认识到张爱玲的不同凡响,在中国二十世纪这种文化环境中,张爱玲真的是太另类了!“可以不顾左派理论的影响,安心培养自己的‘风格’。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式的写作,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确实是独一无二。文革之后,继续革命使人厌倦,人们想停下来过过日子,绘画绣花,请客吃饭了,生活的力量卷土重来,西方写小日子的大师,像乔伊斯、普鲁斯特都翻译过来了。但鄙视日常生活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小传统,积习难返,“过小日子”,一时半载是难于名正言顺的。蔑视倒没有了,但无视依然继续,而且麻木不仁,变本加厉,更现实了。现代化不幸正是建立在这种普遍地鄙视日常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上。所以我国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很少从居民如何在其中过小日子、如何颐养天年考虑。只考虑宏伟、高大、宽阔、欣欣向荣、金光大道之类的形象,等而次之的则考虑政绩、轰轰烈烈搞一把,高升。考虑经济利益,考虑如何卖掉,房子按照商品房设计。别小看这一点,从家的角度和从商品的角度设计房子是有天渊之别的。古代中国的房子是家,现代则设计成商品房了。政绩也是以高大全的形象是否确立为标准。因此,新世界的建设以摧毁日常生活的小世界为代价,毫不可惜。建立在传统和经验世界上的中国日常生活世界被视为落后、丑陋、丢脸、脏乱差。昆明城市改造,几个月就消灭了70多个菜市场。新世界建立了,意识形态的象征在现实中得到表现,日常生活世界也消失了。无数故乡消失了,同质化的新世界席卷中国。根据图纸设计出来的形象,面子、观念、商品经济倒是确立了,但不利于过日子。过日子很难看,很庸俗,很丑陋,很脏乱差。张爱玲说,“生命是袭华美的袍,长满了虱子”。现在,连袍子都无影无踪了。
20世纪后半期,上海有点声名狼藉,说起上海人,大家理直气壮,那些小市民!上海人在这方面也有点自卑,似乎会过日子是一个难于启齿的缺点。但是,生活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人们过日子。在这方面,阳奉阴违是个策略,面子上,宣传上,文化上、市政建设上高大宏伟,意思是“生活在别处”,人们无可奈何,但你总不能不让我低了头喝老鸭粉丝汤吧。只可惜的是,像张爱玲这样理直气壮、信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种老生常谈,将小日子通过文章升华到不朽的文人实在不多。古代文人经常这么做,曹雪芹就是写过小日子的大师。“凤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贾母跟前剥蟹肉。头次让薛姨妈,薛姨妈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让。’凤姐便奉与贾母。二次的便与宝玉。又说:‘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预备着洗手。”庸俗不堪的蟹肉,经曹大师这么妙笔生花地一写,就成了风雅韵事。现在不同,上海人一面过着小日子,就是吃了大闸蟹,也觉得脸上无光,不好逢人就讲的。文人说起上海,言语间还要解释遮掩,总是迅速站到谴责小市民的立场,“比你教为神圣”。在上海一个文人要获得优越感太容易了,骂骂小市民即刻政治正确。其实上海只是二十世纪中国迷信“生活在别处”、反生活的新文化潮流的一个典型,一头生活的替罪羊。二十世纪以降,中国世界对中国经验、中国生活、中国式的过日子的自卑是与日俱增,无所不在的。这方面,中国二十世纪的写作与生活世界之间,真的是有点名不副实。日子过的是小日子,宣传说的是丰功伟绩,我们一直是那样英勇地生活着么?普鲁斯特何时在上海出现?或者像乔伊斯写都柏林那样写写上海,为它立一座日常生活的语言丰碑。这家伙写煎羊腰子和出恭的那一段,真是写得好。
今年春天,我再去上海,出租车从街上经过,我立即感觉到上海出现了某种过去我没感觉到的气氛,过日子的浪潮已经在这个城市理直气壮地卷土重来。中国许多大城市,固然现代、时髦、高大、宏伟、宽阔了,汽车在奔驰,但生活世界的荒凉也是显而易见的。我记得有一回我在北京那些世界最宽阔的大街上奔走了一早上,想找一家卖豆汁油饼的小店,硬是找不到,这种大街不会为小店留下一条缝的。上海自然也免不了为大形象而自我改造,外滩焕然一新,耸入云霄、雄伟洋气。但只要从南京路两侧的任何一条小街走进去,过小日子的浪潮就汹涌而来。弄堂里甚至大街上,各式各样的洗干净的衣服、被褥、乳罩、裤衩从一家家的窗子里穿在竹杠上伸进天空,朝着太阳迎风招展,洁癖者认为这种上海风景很不雅观,我却以为这才是上海的诗意,哈哈,生活的旗帜!电车上,售票员还在使用那种老式的售票本,没有一票通用。看着售票大姐挎着那个塞着各种价格的小票的皮包在人群里穿过来,真像是置身在费里尼的一部电影中。营业了上百年的裁缝店依然在量体裁衣,与时代流行的一刀切完全不同。上海博物馆是免费的!老牌餐馆要预约定座,里面依然有上了年纪的服务生在接待客人,这种服务生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他们把伺候顾客这一行玩到了大师水平,使得许多财大气粗的小人物感到压力。我发现上海又可以无所事事地闲逛了,无数一个式样只有一件的小服装店、咖啡馆、私人菜馆刚刚开业。那把患着洁癖的热衷于凡事一刀切的现代化手术刀在小市民顽强的生活力量面前被磨得卷起刃来,对生活世界日复一日生产着的各种乱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开始用加法,而不是非此即彼。我听说上海对别的城市依然在围剿的小商贩也开始容忍了,真是伟大的进步!张爱玲的上海正在魂兮归来。20年前我去上海,住在一家大众浴室。这次是住在浦江饭店,(原名礼查饭店),始建于一八四六年。一栋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巴洛克式的建筑。饭店介绍说,爱因斯坦、卓别林、罗素、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等名人当年在这里过,曾经是远东最著名的酒店。可笑的是,这只是一家三星酒店,因为旧了所以便宜。旧就是没有档次,低档——这个时代的真理,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巴洛克风格”也不能幸免。我捡了一个大漏,享用了落地窗帘、有着路易·波拿巴时代沿袭下来的风格的高背椅;宽阔无比、光线充足的卫生间、铜质的浴缸龙头以及150年前用小木块拼成的原装木地板,踩上去很有弹性,发出普鲁斯特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响声。后来我到一楼去喝咖啡,味道相当好。那是我五十五岁中的一日,坐在理查饭店的咖啡厅里,窗外是苏州桥,想起1979年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的第二日,我们做了一件事,去找一家咖啡馆,一定要像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喝上一杯。我们终于在人民公园附近找到了一家,那其实是个大众冷饮店,上海滩没有一家咖啡馆!我们坐在蓝色的塑料椅子上,咖啡上来了,那是一杯兑了些咖啡色粉末和奶粉的浓汤,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咖啡,味道差极了。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