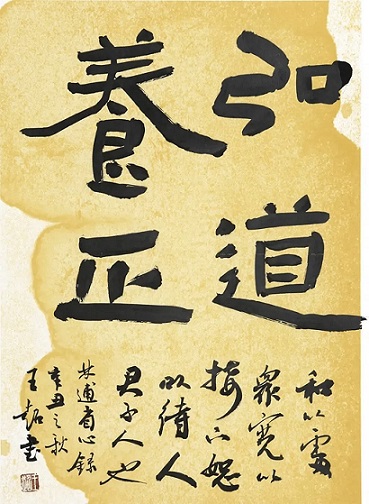1
晃眼间,已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了。那时候,我是上山下乡到海南的知识青年,在生产建设兵团某师担任师报道组组长兼文工团编剧,主要任务是新闻报道、宣传工作和创作剧本。
这里方圆数百里,分布着平原、河谷、山地、丘陵、河流和湖泊,到处都有清冽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那泥土,盖着一层厚厚的腐殖质,黑乎乎的,捏在手里几乎都出油。种什么,什么都茁壮生长,结出丰硕的果实;不种什么,它就由着大自然,愿意长什么就长什么。或者是石梓、黄檀、子京、母生、陆均松等高大的秀木,或者是椰子、芒果、荔枝、龙眼等亚热带果树,或者是各种藤类、灌木、茅草和飞机草,等等。在我居住的茅屋里,便都生长出绿油油的茂盛的枝叶来。
在这片充满生命力的土地上,你养什么,什么就会兴旺;你不养什么,它就由着大自然,催生出更加丰富多采的野生动物来——天上飞的,如飞鹰、啄木鸟、猫头鹰、孔雀雉、棕果蝠、虎斑鸠、绿鸠等;地上跑的,如黑熊、云豹、水鹿、灵猫、金钱龟等;树上攀的,如长臂猿、猕猴、巨松鼠、树蛙、椰子猫等;草里藏的,如山鹧鸪、山鸡、巨蜥、蟒蛇、海南兔等;还有土里钻的,如穿山甲、蜥蜴、大蚯蚓、野兔和蛇类等等。
可惜,大自然赐予这方土地的生机与活力,却被人为地窒息了。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年,感受到的只是无可奈何的荒凉。人们不正常的心态造成了大自然荒凉的生态,而荒凉的生态又使我们维持着艰难的日子。
在艰难的日子里,我们担负着艰辛的劳动和工作。那时候,我常常白天开荒、砍岜、烧山、挖穴,种植橡胶和其它亚热带作物,一到晚上,就读书、采访和写作,经常熬到子夜或凌晨,然后才带深度的疲劳沉沉睡去。当然,最忙碌的日子还是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时候。
每逢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那就是最隆重的盛大节日了。差不多所有的男女老少,都心潮澎湃,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兴奋无比。传达学习最新指示不过夜,是成文或不成文的神圣规定,是头等重要、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夜,将近午夜十二点了,我还在办公室里苦读《资本论》,忽然,师部的露天广播电台传来响亮而清脆的声音——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什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该不会听错吧?再听一遍,没错,没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不知怎么回事,我心情特别激动。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激动时刻,不知道已经经历多少回了,可是,好像这一回更加激动。我很快就解读了自己的心情,因为我比谁都了解自己。这是一种本能的冲动,是久渴的心田喜逢甜蜜的甘露。
饥饿的人们天天祈盼着,祈盼着春风春雨来到这片沃土上,唤醒本该拥有的生机与活力。
如今,这春风春雨终于来临了!
我边听广播,边在办公室里快速来回不停地踱步,热血沸腾,思绪起伏,满脸绽开幸福的笑容……
2
一种神圣而强烈的使命感,像浩荡的春风,鼓动着我那青春的风帆。我又要起锚航行了。
我赶紧从办公室跑回茅屋,麻利地打点简单轻便的行装,一个人便匆匆出发了。每逢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都必须在收听后的第一时间上路,去采访报道先进单位或典型人物,无论在白天或者黑夜,无论山高路远或者刮风下雨,都不能阻止我的行动。与其说这是工作习惯,不如说这是革命事业心和使命感所使然。那时候,实在不需要任何人的布置、指派或安排。最新指示本身就给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作动力。
离开茅屋,辞别师部,踏着熹微的月色,我向着山岭走去。那些年,师报道组六人,全部交通工具只有一架破旧得处处作响只有车铃不响的单车。我体力好,常常放弃骑车的机会而徒步翻山越岭。
今夜,我要去的连队是五团九连,它是兵团表彰的模范连队,连长韦大军是铁人式的模范连长。尽管从师部到九连要爬山涉水六十七华里路才能到达,按我走路的速度计,大约要整整六小时,也就是说要到天亮才能赶到连队,但我心甘情愿。因为这么重要的最新指示的传达、学习和贯彻,只有到“抓革命,促生产”最好的连队去采访,写出来的新闻报道才更有质量,更有说服力。
于是,我满怀信心,开足马力,迈动双腿,爬了长长的一段山坡。气不喘,腿却酸了,怎么啦?哦,今天上云豹岭开荒,从清晨六点起床,山刀抡了十几个钟头,三顿饭都在岭上吃,除了吃饭,所有的时间都在火线上拼搏,砍大树,挖树根,搬石头,砍烧,挖掘树根。那些树根盘根错节,深深扎根于石隙和坚土之中。我们当然先点燃炸药爆炸,但炸后的树根并没有彻底清除,还要人工继续挖掘。而那复杂而坚韧的根系,很快就消耗了我们有限的体力。为此,我每次都精疲力竭。手掌的几个血泡破了,又在破绽处生出第二代血泡,一用猛劲,疼痛自然涌彻心头。浑身大汗淋漓,真个像刚从水里捞上来似的。腿酸手软,饥渴难耐,锄头几乎抡不起来了。就在这时,有人奋然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于是,有节奏的口号声,毛主席语录歌此起彼伏,满山遍野洋溢着革命的豪情和大无畏精神。团部开荒文艺宣传队和师部的毛泽东思想文艺轻骑队也来了,他们鼓乐喧天,好不热闹。他们唱起了一段又一段的革命样板戏唱段,我们全被带着唱开了,一边干活一边唱,好不豪情千丈!我印象最深的是《智取威虎山》的唱段,尤其是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唱段,气冲霄汉,义薄云天,“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难越向前”使我忘却了一时的疲劳,又奋然抡起了闪亮的山刀……
思绪从开荒大会战的工地上收了回来,我又迈开大步,沿着山道爬上了一座山岭,腿更酸痛了。我脑子里一闪:这国民经济要搞上去,联系我们师的实际,除了努力发展橡胶生产,还要搞好工、副业,逐步改善兵团战士的生活吧?兴许以后我们可以多养几只鸡呢!想到这里,我立刻兴奋起来,不觉脚底生风,加快了步伐,忘却了双腿的酸痛和日间的劳累。
星星寥落,月色朦胧,夜色更加沉重了。
山影迷茫,山道迷茫,而我的心间却逐渐亮堂。眺望前方道道荒山野岭,身为夜的独行者,我鼓足勇气,奋力前行。
淡淡的月影渐渐西移……
3
荒山野岭悄无声息地向身后退隐而去,它们藏匿着狰狞的面目,像一群城府很深,工于算计的阴谋家不露声色,默默地、耐心地等待着秋后的算账。
我当然非常清楚,按照当时的规定,每户最多只能自养四只鸡,并且必须自养自用。许多干部,为了带头反修防修,宁愿不养或者只养一两只鸡。我即将前往采访的模范连长韦大军,就坚持只养一只鸡,为的是能下几个蛋,一来招待客人,二来也让他的独生子偶尔尝一尝鸡蛋的美味。
有一位老战士谭石才悄悄养了五只鸡,心想:只要邻居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蒙混过去了。为了混,他经常有意无意地把煮熟的鸡蛋塞给邻家的小孩吃。可是,有个缺德多心眼的人还是把老战士谭石才养五只鸡的秘密给抖落了出来。问题一摆到连部,连长和指导员当然不敢掩盖,于是,谭石才被兴师问罪了。谭石才这条硬汉子,生产劳动绝对是一流的响当当的好把式,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落人后,可这回他被整惨了。他当了十多年班长,向来模范带头,又敢抓敢管,得罪了几个吊儿郎当的懒汉。懒汉们那口恶气吞了又吞,忍耐了许久,终于等来了堂堂皇皇的报复机会。绰号“狗头军师”和“狗尾巴”的两条懒汉一凑合,一张题为《这第五只鸡姓什么》的大字报当晚便贴在连部的大墙上。
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张大字报一夜之间便在全连掀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就传到了团部并且惊动了师部。师政治部立马派我带着小石到九连调查。
那群懒汉拿鸡毛当令箭,拉大旗作虎皮,夜以继日地围攻着谭石才,死死抓住不放,非要谭石才当众回答“这第五只鸡姓什么”不可。一时间,从连长、指导员到普通战士和家属,竟没有人敢站出来替谭石才说说话。不过,我深知大伙的心是向着谭石才的。这么肥沃的土地,这么茂盛的胶林,这么鲜美的草地,鸡群其实并不需要怎么去饲养,只要在屋后草地、林边或山脚搭个鸡寮,清晨放牧出去,黄昏在寮里撒把豆子或谷子,呼一呼,鸡群便乖乖地回了寮。日复一日,换月换季,不多久,仅有几只的鸡群便会壮大到十几只、几十只、一百多只,甚至数百只。但事实上没有人敢于如此放胆去养鸡。假若有,也早被打成资本主义的小爬虫了。可这里,由于得天独厚的天时与地利,鸡群就是繁殖得特别快,真惹祸啊!怎么办呢?聪明的人们不约而同:只养四只,不养第五只。四只全养母鸡,就吃蛋。逢年过节,杀了鸡,有了空额,再补养。也有一些人,养了就杀,杀后再养,反正不超过四只。
我打心底里同情谭石才,就当着谭石才的面对这帮懒汉说:“谭石才这第五只鸡许是马上要杀掉的吧?”说着还向谭石才使了个眼色。可是老实巴交的谭石才并没有领会我的意思,却连连说:“不是的,不是的。”这帮懒汉乘机围上来大声迫问:“那你为什么养这第五只鸡,明知故犯?你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错误?这第五只鸡到底姓什么?”谭石才不敢抵挡,只好当众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养了一条资本主义的小尾巴,表示立即割掉。他一转身,从自家的鸡窝里抓出一只肥硕健壮的母鸡,一刀便割破了它的喉咙,刚刚受惊还咯咯大叫的母鸡在地上搐动了几下,就静静地躺在鲜红的血泊里。谭石才烧了一锅水,三下五除二,脱了羽毛,开了膛,然后将这只虽然姓资但却非常肥美的母鸡亲手送到幼儿园,让阿姨给小朋友们煮鸡粥吃。
面对懒汉们,我忍不住又替谭石才打抱不平了:“你们看,谭石才养的鸡和鸡蛋也不光自己吃呀。听说平时就经常送给幼儿园和生病的同志吃哩。”谁知这帮懒汉们竟振振有词地冲着我说:“林同志呀,你要知道,革命人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4
懒汉们平日里总被谭石才用纪律严加管束,多受批评,满肚怨气,这回看到谭石才当着我的面杀了鸡,认了错,气也消了一些,便不再围攻谭石才,转而围住我这个居然敢于为资本主义小尾巴辩护的年轻人,管你是师部派来的人,只要身上有资本主义的气味,他们就会堂而皇之地批判你,哪怕饿着肚子,也要捍卫“社会主义的成果”,这就是革命者的气节,人穷志不穷啊!
“小林同志,听说你读了不少书,我想请教你”,一个精瘦的懒汉狡黠地盯着我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有三大定律,你应该都知道吧?”
“当然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我沉着应对着他们的挑战。
“现在我要说的就是质量互变规律,量变必然起质变”,他瞄着我,“我们团规定每户只能养四只鸡是有道理的,多养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变了质。”
我笑着说:“每户可以养几只鸡,这是一个动态的数字。现在养四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今后可以养更多,甚至不需要限制数量。当然,这是以后的事情。”
“你在散布唯生产力论!”精瘦的懒汉激动起来。
“够了够了,我今天不是来争论的,我是来搞调查的。”说着,我迈步就走,心里真看不起懒汉。
“别走!既然你来调查,我就反映一件事”,懒汉拦住我,“我们连老罗虽然只养四只鸡,表面上看规规矩矩,可是他却暗地里卖掉了两只母鸡和十多只鸡蛋,听说还卖了好价钱。小林同志,你说,这算什么行为?算不算资本主义尾巴?该不该揪出来批一批?”
“老罗的情况我了解清楚了。他以前从未卖过鸡和鸡蛋,这回是因为孩子生了病,缺钱买药治病,才不得已而为之。昨天,他家里只剩两个鸡蛋,三个孩子争蛋吃,分得不均,打架了。他老婆抱着三个孩子哭成一团,伤心哪!”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老三同志,你脑子里那根弦怎就绷得那么紧啊?”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摆脱了老三和其他几个懒汉们的纠缠。
在深深的黑夜里,爬着弯弯的山道。
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后,或许我们不仅可以多养一些鸡,说不定还可以养猪呢,哪怕每户只能养一头,也是零的突破呵!想到这里,我眼前一亮,旋即,思绪又凝重起来。
我们师一些边远而贫穷的连队,战士们难得吃上一顿猪肉,有的甚至一年整整尝不到猪肉的美味,只是到了大年三十除夕夜,才品尝到一回猪肉。有人笑着对我说:“猪肉就是人参片呀。都一年吃不到猪肉了,真想不起猪肉的味道是什么样了。几回做梦梦见吃猪肉,一张口一块,猛吞下去,那味道比什么都香。吞完了,又后悔不该吞,要细细咀嚼才香哩。”
我清楚地记得,离大年三十还有半个月,在工地上辛勤劳作的饥饿的人们,便禁不住悄悄地议论起除夕将要杀猪的特大喜讯来。尽管工地休息的时候,学毛著,读报纸,有许多政治大事,但人们的兴趣几乎不约而同地集中到杀猪上来:杀哪头肉更多些,怎么煮,怎么分,怎么吃,……谈兴之浓,压倒了任何话题。
除夕终于降临了。全连男女老少奔走相告:大人分四两猪肉,小孩分二两;骨头由食堂熬汤煮菜,再分给大家。那天收工收得早,太阳还没有下山,食堂门口便排起了长队,小孩子特别兴奋。其实,大人们也焦急地等着自己的那一份。四大两,还不少呵。排到我了,双手捧着大饭盆伸出去,双眼睁得大大的。炊事员从大盆里打起了一勺猪肉,这有四大两吗?好像少了点,可他的勺子还在抖动,妈呀,把一大块肥肉给抖回大盆里了,真可惜哟……
这夜,连队小卖部所有的地瓜酒和甘蔗酒全被沽光了。平时从不喝酒的我也沽了一斤地瓜酒,和几位要好的知青友凑成一桌,品肉喝酒,直到东方露出第一缕曙光。
轰轰烈烈的酒肉吃后,半个月过去了,人们仍然不断地回味着。在工地上,在夜谈中,依然是压倒一切的话题……
5
关于猪肉的传说,我还没有说完呢。
从猪肉延伸开来,多少事,都是我听到、看到、甚至亲自经历过的。
在我曾经劳动锻炼过两年多的五连。饲养员曾将一只因病死亡的小猪悄悄拉到后山麓埋掉,谁知这事让连里几个小学生知道了。原来是其中一名小学生悄无声息地尾随饲养员而看到掩埋小猪的一切,放学后约好几名同学,准确地找到掩埋地点,用锄头挖开泥土,挖出小猪,抬到小河边洗净,七手八脚地刮毛、开膛、清洗内脏,然后整猪切块,拾来柴火,烧烤猪肉。这群饥饿的少年抵挡不住阵阵扑鼻而来的肉香的气味,肉只烤得七七八八,还没全熟,就你争我抢,狼吞虎咽,直至一个个干瘪的肚皮都鼓了起来。少年们躺在泥土地上,喘着粗气,实在吃不下去了,才心有不甘地收敛贪馋的目光,想起家中同样饥饿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于是,他们把剩余的肉呀、皮呀、骨头呀,内脏呀,统统收进筐里,抬回家。还没来得及公平分成几份,便成了连队饲养班的被告。这几名饿得发疯的、勇敢而又不更事的少年,还没来得及进学习班接受思想教育,便一个个病倒了。
我实在同情这些孩子们,他们面黄肌瘦,瘦骨嶙峋。他们饿坏了,饿怕了。
孩子们饿了,还可以叫喊,甚至可以哭闹,而我们大人饿了,却不能有所表示,只能默默地忍受。事实上,大人们更加饥饿。每天开荒、砍、烧山;或挖橡胶穴,种橡胶苗,挑水浇水;或种植甘蔗,松土培土除草;或割胶,收胶,挑胶水;或割杂草,拾牛粪,积肥沤肥。每天十几个小时,或沾露爬坡,或头顶烈日,或披星戴月,劳动强度特别大。每天收工的时候,常常手脚酸痛,饥火熊熊。
说真的,我羡慕孩子们,他们无所忌惮,饿了就叫就喊,而我们却必须默默地忍受。我时刻不忘自己是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老战士同样饿呵,可他们还经常关心我们,时不时给我们送地瓜、送木薯、送青菜、送鸡蛋……想到这些老战士,这些可敬可爱可亲的老复员退伍军人,农场第一代拓荒者,我心中就涌动着一股暖流,汩汩地流淌不息……
刚到农场的时候,可能是照顾知识青年,我们经常有改善生活的机会,印象最深的是黄豆燉牛肉,太好吃了。有时是白花花的木薯或黄澄澄的地瓜,大会战时一休息,便热腾腾地吃起来。后来,物质的匮乏使我们改善生活的机会渐次稀少了。我们肚子里缺乏油水,咕咕直叫。于是,来自千里之外的家乡汕头的沙茶或萝卜干炒猪肉便成了我们解饥解馋的不可多得的希望。知青们的默契是:不管谁回汕头探亲,就必须替几个要好的农友们带食物来。人一到农场,这天就是知青们的节日。行李甫一卸下,还没来得及说清楚为谁带了什么食物,所有的行李袋便被围上来的知青们搜了个底朝天。只要是食物,不管是谁家托带的,一律共产共用,附近能赶来的知青全都赶来,到小卖部沽几斤地瓜酒或甘蔗酒,以沙茶猪肉、萝卜干猪肉为主菜,再多煮几盆豆腐、青菜,于是,谈笑风生、气氛热烈的宴会便开始了。知青们吃着、喝着、说着、吹着、笑着、哭着、唱着、跳着,洋相百出,乐极生悲,直至深夜甚至凌晨,仍迟迟不肯散席……
这时,我仿佛看见想象中的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油然而忆起两句诗来:“嵇康对日舞鸣琴,腹中饥火正熊熊。”
6
饱餐了一顿来自家乡的沙茶猪肉和萝卜干猪肉,我实实在在地解了一回馋。回想这几个月,由于刮了几次台风,又差不多天天中午骤降急暴雨,地里的青菜黄的黄,烂的烂,只有冬瓜大丰收。食堂大饭厅的一角,堆的尽是大冬瓜,像小山似的。几个月来,几乎顿顿吃冬瓜。怎么吃?将冬瓜切成片,用滚烫的开水烫熟,打捞上来,拌以咸而不香的酱油,便是我们下饭的唯一的菜了。偶尔,开水烫熟的冬瓜片拌点葱花,再小心翼翼地滴上几滴极为稀罕宝贵的猪油或花生油,那就幸运了。如果实在吃厌了,不想再吃那冬瓜,就只能在开水里洒点酱油,用酱油水下饭了。
吃了几个月的开水冬瓜,我们几个要好的男知识青年暗地里一交流,才知道大同小异:大家都发生了怪毛病——“小弟弟”都老实了,不论白天黑夜,都是垂头丧气的,没有了阳刚之气。
在那段冬瓜总是独霸餐桌的漫长的日子里,有时候,比如十天半月,竟有一顿是空心菜!当然也是用开水烫熟,再拌点酱油。但不管怎样,光看那惹人的绿色,便会引起那种古老的、原始的、本能的、强烈的冲动。不过,我和几位知青友相约,每逢发现这种难得的机会,便故意推迟下班,慢进食堂,把机会让给那些正在长身体的可怜的小孩子。
我曾目睹过几次这样的情景:一对小兄弟争着到食堂打菜,互不相让,以至打起架来,哭哭闹闹,这时,食堂必有空心菜!开始,曾有一次我排队买到了绿得惹人的空心菜,正庆幸自己今天有口福,这时,听到背后传来孩子失望的哭声,原来他贪玩,慢几步来食堂,排到菜窗前,恰巧空心菜卖完了,只剩白花花的令人寒心的冬瓜,孩子伤心地哭了。我赶紧将小菜盆里那份可爱的空心菜送给了孩子,孩子起初很羞涩,不敢要。“给!趁热拿回家里吃。”在我的再三鼓励下,孩子礼貌地接受了,连声说:“谢谢叔叔,谢谢叔叔!”感激地走了。我呆呆地站在食堂大门外,想了许久,眼睛渐渐模糊了起来。这天晚上,我就向知青友们提议,再饿,也要把这种机会让给小朋友们。
一天下班,我走在路上,忽然一个小孩子拦住我,拉着旁边一位大人说:“爸爸,这就是我说的那位叔叔,他把空心菜让给了我们。”那位大人迎上来,热情地拉住我的手:“哟,原来是小林呀,孩子回家总说那位叔叔好,真感谢您。小林,晚饭不要上食堂啦,就到我家吃面条去。”老韦热心地邀请。“老韦,谢谢,不用啦。我们几个知青已经约好先打半场篮球,再吃晚饭。”说罢,我就匆匆来到篮球场。
打完篮球,我们几个球友正准备到小伙房,动手煮点冬瓜汤,加点沙茶猪肉下饭。谁知韦连长带着孩子小韦来了,硬是拽着我们到他家吃面条汤,说是煮好了,全家等着哩。不去,不能去,怎能去呢?来来来,怎能不来呢?不来还对得起我老韦吗?盛情难却,我们四个知青友汗淋淋地来到韦连长家。韦连长的妻子给我们每人盛了一大碗葱花面条,还放上黄澄澄、香喷喷的大荷包蛋。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这时,我的双眼又模糊了,眼角悄悄绽开了难见的泪花……
虽说是在荒凉的生态环境中艰难地生活着,可是,我这颗热血沸腾的火热的心,却从来未曾荒凉过。
作者简介:林继宗,男,中国学术发展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潮人文学艺术协会会长,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学术顾问,美国风笛诗社成员,国际潮人文化基金会荣誉董事长,中华散文网创作委员会副主席,广东省潮汕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签约作家,中华诗词博士,原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汕头市作家协会主席,潮汕星河奖基金会名誉会长。已经出版各类文学专著22部,共1079万字,先后获得全国大型征文活动优秀系列长篇小说一等奖、中国散文精英奖、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年会一等奖等国际、全国、省部级等各类文学奖106项。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