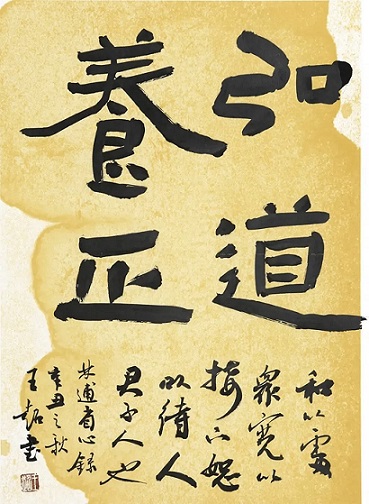从发表作品的数量来看,小说队伍确实在经历更新换代。70、80后势头正猛,90后也不示弱。40、50后作家露面的次数日少,60后作家也日渐稳重矜持。但也有特殊,已经八十高龄的王蒙先生,贡献了中篇《奇葩奇葩处处哀》和短篇《仉仉》,文思依然泉涌,确是宝刀不老。冯骥才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暇,无法拒绝小说的诱惑,奉献了《俗世奇人新篇》,其中的《甄一口》接地气,喝酒也是中国特色民族气派,乐煞人也。
姚鄂梅、孙频、阿袁、少一等作家,近两年来保持高产势头。2015年,姚鄂梅《傍晚的尖叫》《天际花园的私房菜》《红颜》,紧盯当下,证明了她的产能和长跑实力。孙频的《无极之痛》《柳僧》对生活悲剧层层加码,越写越狠。特别是尹学芸,一口气推出了《祥瑞图》《隐藏》《呼拉圈》《鱼在水里游》《士别十年》等多部作品,是她名副其实的高产年。
一些有特点的作品让人难忘。
张欣《狐步杀》是好看小说的典型,近于一个小长篇,读下来却一点都不累。
张翎《死着》将眼光投向交通事故的处理及其引发的现实悖论,是作者的一次华丽转身。
吴昕孺《中国小脚》有一种西方文化眼光,语言精致,细腻,毕肖一个外国人写的中国故事,别有一番风致。
格尼《和羊在一起》是地道的人性悲剧,是对玩弄手腕、背信弃义者的血泪控诉,在揭示乡村人性的深刻方面,直逼鲁迅。
西元《死亡重奏》几乎是军事题材小说中最优秀者,战争历史被处理得既诗意,也当下,还有情怀。
阿来《三只虫草》写一个孩子对人世的想象与质疑,有丰富的主题和思想含量。
海外华人陈九的《跟尼摩船长出海》是关于跨文化的叙事,以豪放粗犷的语言讲述海外华人在美国的经历,反映出中美文化上的冲突,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前沿性文化想象。
常小琥《收山》让人联想起老舍风格,讲述关于老北京烤鸭行业的师徒关系与技艺传承,语言老到,厚积薄发,京味特色鲜明。
苗炜《面包会有的》简直就是全球美食大全,应有尽有,纸上盛宴。
苏兰朵《白熊》是作者“我也来玩一把科幻”的转型尝试,故事新颖,叙述新潮,也不乏科技制约人性自由的思想作料。
阿袁《上耶》是她近年来高校小说的代表作,叙述随心所欲,左右逢源。
潘绍东《月亮上的稻草》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前嫖客遭遇前小姐”,其实是写一个吃软饭的男人的遭遇与官场规则。语言幽默是最大亮点。
鲁敏《三人二足》重口味,够刺激,表面事关恋足癖,实际上是毒品犯罪。
陈集益《人皮鼓》是年度小说中最让我揪心刺痛的,叙述一个打工仔由好变坏、杀人成性、拿人皮做鼓的事故,显然是出离于愤怒之后的发愤之作。
宋小词《锅底沟流血事件》讲述农民拦路收费,自酿悲剧,揭示小农意识一针见血。
霍艳《离弦之箭》有关顾凶杀人,有《今日说法》的味道。
梁晓声《地锁》和陈鹏《车位》都是有关停车难的现实表述,很接地气。
于昊燕《狗奴》讲述丁克一族的婚姻与对狗的“忠诚”,结尾句写得最漂亮:“仔仔(狗)一直没有找到。有人说它成了狗皮大衣,裹着女人丰满香艳的肉体,有人说它成了狗场的种狗,过着纵欲为生的日子。”
还有许多作品都不错。比起余秀华的诗歌来,小说的爆发力似乎有所减弱。我更愿意将此看作小说的沉潜。它在积蓄力量。这当然是对有准备、有野心的作者而言。实际上,诗歌评论也好,小说评论也好,应当越来越集中于对好作品的挑选和批评。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来看,好作品被冷落、被遮蔽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在这个市场化主导一切的时代,能耐得住寂寞、排除各种投机诱惑、安静阅读利润低下的诗歌、小说,本来就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读到佳作能说出来,就更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批评不为朋友捧场,不为红包引诱,不牵挂稿费,不囿于圈子,确实很难。然而,那些在祖国大地上闪光的好诗好文,那些在各处吸引我的文字和灵魂,时时让我不能平静,即使读过数月、半年、一年之久,仍在我的心间闪现,我不能不说。
中篇小说据说是近十几年来最能代表文学创作水准的领域。大批刊物、作家都将主要精力放在此处。因此,中篇小说的规模和产量都在逐年上升,在期刊的位置也是独占鳌头,无可替代。一年下来,起码在两三百部以上。中篇既是作者的重点投入项目,也是读者的重点期待。
2015年特别让我有话可说的,是两个作家的两部中篇,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和蒋峰的《翻案》,这两个中篇可以看作70后、80后最新的代表性作品,是年轻作家展现锐气和锋芒之作。“两峰/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创作取向,《地球之眼》向现实获取灵感,《翻案》向历史汲取力量。
《地球之眼》不仅是2015年度小说的重要收获,恐怕也将是新世纪以来中篇小说的上乘之作,是继《那儿》《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之后,又一部直面当下社会问题的力作。它直面当下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呈现了当今社会令人揪心的道德困境。不是一部和稀泥、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梦之作,而是一部你难、我难、他也难的惑之问。小说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抓到了当下中国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穷人与富人的分野,物质与精神的冲突,经济与道德的冲突。“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是不是失效了?”这一“天问”贯穿整部小说,特别能引起我的共鸣。不仅揭出安小男所代表的吊丝们的病苦,还揭出了李牧光所代表的官二代的病苦;不仅富人李牧光心狠手辣,穷人安小男也绝不心慈手软。对立双方没有胜利者,穷人富人都是失败者,都是道德的摧毁者。这是小说的悲剧力量所在。它超越了敌强我弱的叙事模式,抛弃了单纯的悲情渲染,将着眼点放在矛盾冲突的上一层,即形而上的道德层面。它关注现实的矛盾冲突,但更关注矛盾双方所共享的恶的逻辑。这个逻辑恐怕是有普遍性的。像那些毒奶粉、毒鸡蛋一样,安小男、李牧光精神中的毒素一点也不逊色,它好像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食品,无法摆脱,又无法安心。道德的恶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我们时代的悖论。《地球之眼》的用意正在此处,它要以监控摄像头的方式,展示我们的精神困境。这是小说让我刮目相看的所在。小说点到了我们时代的痛处,揭出了新的全球化、市场化时代中国的病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地球之眼》超越了问题小说的框架,超越了“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里,重新结构人与人的关系,重新定义阶级的关系,重新思考人的道德问题。尽管并不能给出答案,但问题本身已经足够精彩。它或许预示了小说的一种新趋势。也预示了中国小说未来所具备的世界价值。我看到几本重要的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都转载了这部小说,正说明小说的锐利触动我们这个社会麻木的神经。
另一部重要作品是蒋峰的《翻案》。这部作品似乎没有《地球之眼》那样惹眼,似乎有些冷落。但我坚定地认为,这同样是一部重要作品。这部作品最重要的启示是,让我们重要看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小说有能力重写历史,某种意义上,小说甚至大于历史,这显示了蒋峰作为小说家的野心和力量。它让我惊讶的地方很多,叙事的精确,视角的变换,情节的旁逸斜出。他不按常理出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人物上场眼花缭乱,秩序却井井有条。锐利的穿透力,宽广的辐射面,使它像一枚能量很大的放射源。不光能看到职场、官场、凶杀、爱情、悬念,这些当下小说和电影司空见惯的标准配置,还能看到“历史”、“现实”、“真实”。当然,后面这老三样,通常被时尚的写作者们认为过气了,是所谓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一“陈旧”写作系统中的配置。这老三样往往是令人头疼的高墙。蒋峰以他的叙事轻功,翻越了这几堵高墙。我有非常奇怪的阅读感受:故事既简单又复杂;既是大杂烩又是有机体;时间既流动又静止;空间既封闭又开放。既打开了虚构之门,又打开了真实之门。最重要的,既玩弄历史,也玩弄真实。蒋峰确实是在玩弄“真实”与“历史”。“历史”不断向“真实”挤眉弄眼:你怎么看我呢,你怎么用这种眼光瞪着我呢?假做真时真也假。已经很难分清这个杀人犯的故事是真是假,是虚构还是历史。如果薛至武、詹周氏是假的,那么,张爱玲、胡兰成、苏青是不是假的?周佛海、胡兰成是真的,施拜休、徐沛东是不是真的?小说令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去仔细研读有关胡兰成、张爱玲、苏青、周佛海等人的生平资料,仔细研读日据时期上海的历史。当然,这个冲动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便消失了。我自己哈哈一笑:有点上当受骗。有研读的必要吗?没有这个必要吗?
为什么《翻案》能让我产生如此纠结的想法?我觉得是它的写作观与众不同。这个写作观就是,历史中的现实就等于真实,或者反过来,找不到现实的历史必然是不真实。现实就是历史中真实的部分。小说的重要功用之一,就是帮助、引诱、或裹挟读者寻找历史中的现实。至此我们就不难明白,小说既要包含历史,还要包含现实。说白了,小说大于历史。以假乱真和以真乱假,历史与虚构让人无法分辩,但历史的真实,詹周氏、薛至武这些人物命运的真实,却让我共鸣。《翻案》叙述了一个有关“历史中的真实”的故事,演奏了多个人物的命运交响曲。蒋峰一向偏爱悬疑,许多评论者注意到了这点。但这部以悬疑为噱头的小说,突破了悬疑的框架。不仅仅是案发杀人,查找凶手,侦破,审讯,辩护,反复,执刑,这些我们在各种狗血剧里司空见惯的元素,还牵涉到了阴谋,爱情,权钱交易,政治变节,民族大义等多个主题,特别是历史巨变。《翻案》很有《活着》的意味。杀人疑犯詹周氏,由本来的死刑犯变成了延年益寿的九十岁老太,昔日风光无限的警察局长薛至武,解放后成了镇政府的司机薛师傅,日据时期大红大紫的畅销书作家苏青,成了看大门的老太太。这些人物命运的戏剧性,一点都不输于《活着》里边的龙二、福贵。用小说中的原话是,“三十几年从宣统到北洋,从租界到汪伪,从民国到解放,王朝更迭,你永远都不知道你明天的命运如何。”这种今不知明的历史体验,恐怕正是《翻案》要寻找的历史中的现实。薛至武的命运最具神秘色彩,也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者。按道理说,他是日伪上海的官员,本应以汉奸论处,但却侥幸活了下来。更为奇妙的是,解放后他依然较为幸运。“事实上连薛至武自己都想不通,自己怎么还不死,新中国解放,五六十年代毙了那么多人,政委也没找他谈话。也许是从1945年就一直在提篮桥坐牢的关系。”警察头子,汉奸,军统卧底,国民党的敌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汽车司机,这多重身份重叠在一个人的身上,该是怎样的戏剧性?这种历史的戏剧性让人无从把握,无从知晓。从细节来看,薛至武的命运奇迹,戏剧性色彩过于浓厚,不能言之凿凿地给出他不死的理由,多少有点避实就虚,有过分依赖叙述空白之嫌。但反过来想,如果小说言明理由,恐怕效果大打折扣,小说拥有的历史神秘感、整体气质将不复存在。
个人命运与大历史的结合,仅是《翻案》的一个维度。还有更多的维度。人性的维度,法治的维度,妇女命运的维度,社会良心的维度(这个主题在石一枫《地球之眼》中有精彩的呈现)、民族主义的维度等等,每一个维度都能打开新的解读空间。就拿法治维度来说,这是我们文艺的软肋。中国谈法治已经多年,但是在文学作品中,法治话语严重缺失,这是非常有症候性的。陈源斌的《万家诉讼》几乎是个特例。近几年来,我读过的以法治为主题的小说仅有艾玛的《初雪》,探讨前苏联的法学思想和中国的法律实践。蒋峰的这部《翻案》,建构了一个相当精彩的错案案例,不能不让我想起呼格吉勒图案或聂斌案。围绕詹周氏杀夫案所展开的法律实践证明,法律仅仅是一个装饰。薛至武拿手电筒在这个女人身上色迷迷地照射的场景,所呈现出来的法官/色鬼、女犯/女色的角色互换,有不可抵挡的穿越历史的生命力。
《翻案》也让我想起《三国演义》。几百年来,《三国演义》一直在扮演历史真实的角色,它大于《三国志》。它既可以做历史参考书,也可以做官场指南,也可以当商业宝典。《翻案》是不是可以既当婚姻史读,也当法制史读,还当社会史、思想史读?下这样的结论可能为时尚早,但它的确包含多种解读的可能性。《翻案》当然不是《三国演义》,《翻案》的着眼点不是重大历史事件,而是被重大历史掩盖的人的命运轨迹。表面上是小人物,平民视角,实际上思考的还是大历史规律。《翻案》有双重含义,翻詹周氏杀人的小案,也翻现代史的大案。《翻案》呈现了小说对历史的新理解。
小说本来就是虚构,这已经是当代文艺理论的常识。按理说,我不应当陷入有关真实与虚构的纠缠之中,不应该再有以上这样纠结的阅读心理。从1980年代的先锋派小说以来,人们早已适应了放弃对大历史的追问。马原、格非、莫言、余华等人早期的小说无不如此。先锋派小说故意抛弃原来所谓的大历史,特别是像“三红一创“那样的大历史叙述。即使陈忠实的《白鹿原》涉及近现代百年史,但它所提供的历史图景,也与我们原来理解的历史大相径庭。可以说,几十年来的小说烦透了大历史,虚构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近在眼前的例子就是抗日神剧,石头打飞机,裤裆里藏手榴弹,虚构已经荒诞到了脑残才会相信的程度。小说要么不写历史,要么把历史当妓女,这种写作伦理充斥市场,竟然大量的人买账。从理论上讲,一切历史都是叙述,一切历史叙述都是虚构,但此虚构与彼虚构不是一回事。追求还原历史真实的虚构,与用历史装点门面贩卖私货的虚构,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蒋峰属于后者。他当然是先锋派的徒子徒孙,也吸收过新历史主义的营养,但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叛逆者。他依然有探究历史真实的冲动。他重新回到历史上空。他想为我们熟知的历史翻案,换一个字眼,重写历史。重写他眼中的历史真实。我不知道蒋峰在何种意义上看待这种虚构的历史真实,但我认为,他对历史的认知,有与众不同之处。历史不仅仅是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仅是周佛海、汪精卫、蒋介石式的名人史,还是薛局长史,是詹周氏史,是律师施拜休史。仅此一点,蒋峰的这部《翻案》已经不仅仅在为一个虚构的人物翻案,而是在为小说的功能翻案了。它让我们警惕“纯文学”的洁癖。
与蒋峰《翻案》旨趣相近的一部小说是王璞的《西河湾》,以一个潜入大陆的国民党特务的悲剧一生,来重现历史被遮蔽的部分,颇耐人寻味。
红日的创作一直从基层实际出发,汲取灵感,去年的《报道》让我记忆犹新,今年他又不出意料地推出了《考评》,完全是一部有关机层单位年终考评大全,看得让人啼笑皆非。从他的创作谈中得知,他绝非虚构。
短篇小说按一种经典的说法是生活的横截面,它不仅在篇幅上比中篇要小,而且更难写,艺术性要求更高,是衡量小说家艺术水准的准星。就我看到的几十部作品来看,仍然有些短篇佳作。
麦家《日本佬》是我看到过的他的第一部短篇。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大语境中来读,别有意味。这其实不是一部抗战小说,也算不上历史小说,只讲述了一个曾经被日本人抓丁、后又释放回来被揪斗的人的悲剧命运,小说深刻的地方不在于被批斗的故事本身,也不在于其呈现出来的民族情结,而在于所描述的“莫须有”原型,和所包含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加害于人的社会心理,这个原型心理,让人心有余悸。
杨少衡《你没事吧》是反腐语境中,对官场心理的一次精细呈现,也是杨少衡小说的一个新的开掘。没有多少曲折的故事,更多高压形势下的官员心理的起伏,多少年后回头看,这部作品算是一个当代写意。
蔡骏《眼泪石》有点穿越,也有点玄幻,把阅读经典的感受,打工女孩的人生遭遇,和自己的情感记忆合在一处,穿越,情感线索还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眼泪石”的形象蛮吸引眼球的。实际上就是些小感想,但写得放松,随意,讲出了一种心理真实感,反而觉得比许多苦心孤诣、搜肠刮肚、关注现实写出来的东西更好玩更真实。这个感觉很奇怪,就像我在朋友的推荐下读网络修真小说《飘眇之旅》,这种作品虽然是胡思乱想,异想天开,但它在骨子里是接地气的,是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人所想所思,它的飘渺并不飘渺,反而比许多“现实”更现实。
祁媛《奔丧》展示了80后作家完全不同的眼光,这部作品提示我,新一代作家真的不同。小说讲述一个侄子为风流的叔叔送葬的故事,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可怜叔叔,包括叔叔的妻子,孩子,他的丧葬竟然像做一道菜,毫无感情,按工序完成,每个人都觉得与自己无干,这个世界的冷漠,令人吃惊。小说把丧葬的每一个细节都交待得很细,是典型的客观叙述,并无多少技巧,但每每都有惊人之处,因为,死亡在新一代作家的眼光中完全变了,这个社会完全变了。百年文学史上的死亡,从未如此冷漠过。这件事本身就令人震惊。
同样令我吃惊的是80后作家庞羽《佛罗伦萨的狗》,一个小女孩初中生勾引男人的故事,写得很暧昧,又很冷漠,好像缺少是非观念,这个很令人吃惊。这个女学生第一次有点被迫,后来主动,大叔与她的故事又像洛丽塔,不清楚是想说好还是坏,结尾又有点憎恨。整体上叙述朦朦胧胧。
乔叶《塔拉,塔拉》以驴友的形式,讲述旅行中的人物,一个在内蒙古遇见的汉子,豪爽,不文艺,但热爱生活,细节很好,散文一样的句子闪耀着作家深厚的文字功力,许多独特的见闻,对狗的看法,对养殖业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观念。
张楚《忆秦娥》是一篇艺术手法非常老练的作品,写一个被抛弃的女子,一辈子爱一个男人,虽遭百般屈辱也不离不弃,写出了中国女性坚贞顽强的性格,意境也很美。
此外,余一鸣《稻草人》和田耳《金刚四拿》思考城市化时代农村文明的式微,陶丽群《母亲的岛》是作者对拐卖妇女生活处境和心理的近距离观察,甫跃辉《普通话》有对语言在当下生活中的位置的思考, 于一爽《十年》对新一代青年男女情感世界的纠结的呈现,都值得关注。
最想谈的是葛亮《不见》。葛亮是近年来重要的小说作家,有人说可望“成为两岸三地极具大将之风的小说名手”,有非常好的艺术准备。这一次,他采用一种新闻事件式的框架,让图书管理员杜雨洁逐渐走入这个框架中去,由旁观者变为当事人,非常有带入感。爱情加悬疑的套路,吸引眼球。明里约会,暗中跟踪,一步步逼近真相,吊人胃口。手法极其细腻,叙述极度有耐心,就像一个等待猎物的老手等读者上钩。然而,我读了之后,总觉有点不对劲。戏剧性太多,就令人生疑。一个绑架女孩的男人会钢琴,风度极好,这个就不必深究,关键是,他绑架了市长的女儿后,依然在城里像没事人一样教钢琴,然后,又若无其事地让图书管理员杜雨洁爱上他,再进而把杜雨洁骗上床,绑架,还挖了一个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式的地洞,天哪,这故事太有点好莱坞!都是抽空了社会环境的虚假叙事。不用说绑架了一个副市长的女儿,就是绑架一个老板女儿,也不可能这么招摇。但是,如果把小说放在香港,似乎香港不存在“副市长”,跳《最炫民族风》广场舞的“中国大妈”好像也是大陆风景。因此,越发不能让我怀疑其现实依据。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如此处理?显然是为了艺术、阅读快感之类的宗旨。小说都是虚构嘛,这成了近年来人们深信不疑的文学的尚方宝剑。网上看到几个评论,也谈这个小说艺术手法如何精湛,构思如何精巧,表达人物的内心是如何的深入。这些我都承认,但我还是忍不住要问,这样的作品,它的生命力难道仅仅在于向壁虚构?仅仅在于为艺术而艺术?男主聂传庆倒是颇有意味,他的作案动机,是为了报复市长夺走他的爱人和儿子,能说得通,但是,再绑架杜雨洁又是为哪般?我脑洞想穿,也没想出来,莫非聂传庆是性虐狂,莫非市长女儿与聂传庆合作绑架杜雨洁,是要为自己找个替罪羊,好让自己开脱?小说没有交待这些,而是像先锋派小说那样留了个白。有一点是肯定的,小说把聂传庆塑造成了一个英雄人物,玩钢琴,有魅力,草根气质,吊丝遭际,这个比玄幻更为玄幻,比邪乎还要邪乎,真不知该怎样说当下的小说了。葛亮的这部小说,相当症候性地呈现了当下小说的困境,即在艺术突破与处理现实生活之间的巨大困境。
小说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是1990年代以来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尖锐的情形下,文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像“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新世纪以来的《那儿》《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一个人的遭遇》,包括今年《地球之眼》,都是这方面的文学的回应。而另一个方面,小说在经历了1980年代先锋派潮流之后,在“怎么写”方面同样也创造了中国文学“三十年走完西方文学一百年”的奇迹。除了早期的先锋派作家,小说界苦苦探寻艺术的作家不乏其人,宁肯,李浩,晓航等,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可以说,小说在反映现实和艺术两个方面都有长足的探索,但是,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至今仍是个难题。小说的“小”是当下小说的软肋。温铁军在他的经济学著作《八次危机》中曾戏言,真想写一部雨果《九三年》那样的小说。这当然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梦想。小说家是否也有过相似的梦想,想写一部《八次危机》所涉猎的当代中国经济史那样的小说?不是说大就一定好,但小说不应当排除大,家国情怀是一种文学视野,是一种理想,也是我们当代人的生活处境。我们已经不生活在封闭、保守的小农田园时代,也不是在小山村里终其一生,而是在网络弥天、高铁纵横、私车乱奔的时代里穿梭、奔波、打拼,全球只是一个村,这个感觉在突发事件新闻化、恐怖主义本地化、空中打击游戏化的今天,有越来越切近的体验,但这些体验在小说中鲜见其踪,这不能不让人遗憾。就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些领域来说,法治、养老等题材,一直鲜有力作。以法治国提了很多年,但这方面的小说佳作在哪里呢?一种观念,在它没有进入世俗生活之前,都很难说它是真正的观念。我的印象中,有一位艾玛的作者,写过一篇《初雪》,这是近十年来我记得的有关法治问题的唯一小说。高考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电影《青春派》是一部反映高考的佳作,好像已经没人记得了,但小说却鲜有涉猎,不知原因在哪。
【免责声明:本站所发表的文章,较少部分来源于各相关媒体或者网络,内容仅供参阅,与本站立场无关。如有不符合事实,或影响到您利益的文章,请及时告知,本站立即删除。谢谢监督。】
发表评论
推荐资讯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