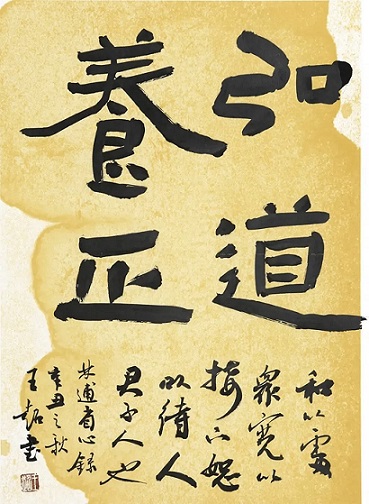冬末的太阳早已缩进山坳子里去了,油灿灿的光染亮了天边的闲云,又细致地给彩云描上了金色的丝边。陈老太家的瓦檐上给余晖抹上一层淡金,就连屋顶上青灰古旧的板瓦也被润得暖暖的,泛着古朴的味道。
在这个滇南县城僻静的角落里,这样的瓦房怕也是难得一见了。就拿陈老太的家街坊来说吧,无论是大叔大婶,大爷大妈,都日夜操持着自家的买卖。很快,陈老太的邻居们个个盖起了钢筋水泥的小楼房,家家户户,气宇轩昂。憋足了神气的王家老倌,现在也敢和社区的小主任叫上一板。每当居民社区开会,王老倌总是第一个赶到,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因为这里最显眼,叫人家看得明白。
然而在这里,陈老太却是个例外。
陈老太今年六十二了,老伴儿是个中学英文教师,可十年前就先她而去了。陈老太不是个懦弱的女人,她有双能干的手,洗衣,煮饭,纳鞋底样样在行,她膝下的两个儿子也在她一天天的拉扯下长大成人。
那时的陈老太很精神,整天有使不完的劲儿,忙东忙西,忙里忙外。她脸上的皱纹很少,那皱纹仿佛也知道老太的心思,故意耽误了几年才来老太额上报道。
那时,老太的儿子们正在读高中,学费不算很贵。老太整天乐颠颠地在邻居面前夸耀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会儿夸老大心好,一会儿赞小儿子听话,仿佛天上的宝贝一般。可儿子们没想到,邻居们也没有料到,就连陈老太自己也没敢想过——儿子出事了。
出事的原因很简单,就像老太儿子们的头脑一样简单。
一个毒贩子使了五十块钱,让老太的儿子把“药”送给一个“病重的大叔”,结果刚转了个墙角,就被守在那里的民警抓了。按理来说,未成年人犯法可以减轻处罚,但十分不幸的是,他们今年刚满十九岁,已经过了非常保护期。
这就是政策。法律是公平的,自然要按照条例来执行,这也是政策。
陈老太初闻噩耗,险些背过气儿去,悠悠转醒,哭得昏天黑地。那时的街坊很热心,一个个都来探慰老太,出门进门,络绎不绝。约摸过了个把月,细心的街坊发现老太的眼泪似乎少了许多。她时常一个人倚在自家门前的石墩上,两眼直直地瞅着檐下的燕巢,嘴里喃喃地蠕动着,似乎在质问燕子春来了为何还不归来。
打上次大规模的安慰过后,已很少有街坊来过这屋子了。连平日里最与人亲善的黄二嫂子——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女人,也很少敢大跨步地揣着针线活从这里经过了。据黄二嫂子后来讲,陈老太有两次本想与她打招呼的,但她怕多说话又会累着老太,因为她说陈老太要多休息。街坊们听了个个点头,唔,是太累了,要多休息。
陈老太记得很清楚,唯一一次是社区主任来过,那次是来调查一下各家的家庭情况。主任叼着半截儿烟,用眼在屋里屋外扫视了一圈之后,嘴里哼唧着对随行的秘书说给老太记上,这个情况啊,基本符合补助标准。说完就带着秘书转到别家去了。
半年过去了,陈老太一分补助的影子也没看见。也许是政府资金不足吧,陈老太想。
然而陈老太越孤单,越是少有人敢过问。老太的门前依旧人影难寻。
说实话,陈老太家的房子不算很破,因为她老伴在世的时候总是在屋顶上敲敲打打的。只是自老伴走了以后,连瓦崧,蒿草这样的野草也欺负到老太头顶来了,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可怜的房顶。
记得有一次,他们家土墙的东角被连续几天的大雨冲缺了一个大洞。老太说怎么办呢,她老伴就说不急不急,想了想,就把门前那个废园子的半堵砖墙拆了一半,用拆下来的砖把大洞镶了起来。
墙还没有怀,老伴就先去世了。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家的房子再也没有受过大的创伤,老伴当年拆剩下的那半堵断墙至今也没有人碰过。
就在陈老太“贱妾茕茕守空墙,忧来思君不敢忘”的时候,那座荒废多年的园子却被另一家人买了过来。
起初的那两天,只见几个穿白背心戴草帽的高大汉子在废园里忙活。他们手中各持一把亮闪闪的镰刀,唰唰唰几下,就把里面的野草全部放倒了。陈老太很心疼,心想割了多可惜啊,有的还可以做草药嘛。
两天后的一个清晨,陈老太照例大清早的就坐在门前的石墩上,探着脖子往废园里张望了。今天似乎很意外,她隐约看到园子那头有个老太太,再仔细辨认时,果然是一个老太。这老太约摸六十余岁,和自己相差不大,然而衣着打扮,显然是富贵人家。一头银发,满目慈祥。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中年人搀着,照打扮,倒有七分胜过那社区主任。
两个中年人一口一句妈,把老太太乐得直打哈哈。看到这里,陈老太不觉心中一酸,要是自己能有这样孝顺的儿子,那该是多好的事。
就在陈老太低头自叹的空当儿,对面那老太太已经看见了她。
嘿!对面的老人家,你好啊?那老太兴奋地朝她招着手,腕上的小金镯子也顺势朝肘上滑下来。
陈老太一生从未对人说过你好这样的文明词,也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即使是她教书的老伴,回到家也是不改一副坐办公室的派头,哪里有过什么文明词。
兴许是被那老太的金镯子幌花了眼,也许是初听这文明的问词儿,她倒愣愣地答不上话来。
哎呀呀,老亲家(一种亲近的称呼,并非特指儿女婚事)。遇见你真好啊。她没顾陈老太的呆愣,又补充道,我早就想找个人说说话呢,年轻人的话我可不爱听。
她未及说完,一个工头模样的人小步跑到其中一个儿子跟前,揭了草帽,压低头说道,书记,这(手指那断墙)是公共的,您看拆是不拆?
未等那中年人开腔,老太太一把扯住了儿子道,柱儿,咱们不拆!你妈我在家的时候,可以和这位老人家说说话。妈的腿脚不灵活了,心也不至于不灵活了吧?
妈,您说哪儿的话!不拆就是了,您老安心吧!柱儿安慰着。转过身来便呵那工头道,听着,叫他们别乱动,少了一块砖,就算你头上!
是,是!听书记您的吩咐。工头哈着腰过去了。
陈老太听了这话,想到这老太还真有意思,居然为这事骂儿子。当下心中欢喜,就冲着对面那老太笑了一下,那老太也回了一个笑,转身由儿子们搀回去了。
打那日起,陈老太只要一坐在石墩上纳鞋底,就会不时地探头往园子里瞅。看看工人们干活,在他们得闲时说上几句话,问问房子怎么建呀,打算盖几层之类的零碎话。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半年过去了,三层的小洋房终于盖起来了。尽管房子的模样在陈老太心中辗转了几千遍,但建起来的时候还是着实让她吃了一惊。在她的心里,这恐怕这是最好的房子了。她忽然想起在老伴书上见过的一张画,上面是一幢白色的小洋房,讲究,气派,衬着天空的碧蓝,托着草地的嫩绿,很是好看。
她瞧得真真的!
可眼前这房子不比那画上的好十倍么?就算她教了大半辈子英文的老伴,也不曾见过这样好的房子!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陈老太照旧大清早的就倚在石墩上纳鞋底了。这时候,她发现对面阳台上的门开了,那天的那个老太居然立在门前。
嘿!老亲家,我在这!先招了手,她的手光秃秃的,只看得见几根暴突的老筋伏在干瘦的手上,活像条脱了皮的干树杆。
哎呀呀,你早啊!老亲家,又看见你了。那老太太高兴得露出几颗银闪闪的牙来。
唔,您家姓什么啊?陈老太又问。
姓张!你叫我张妈也得,张老太也得,张老太太也得!呵呵,反正就是姓张。你呢?张老太笑了起来。
叫我陈老太吧。陈老太平静地回答。
就这样,两个老太之间的话一发不可收拾,天天聊,天天都要聊。隔着断墙,有人在意听你的话,但绝不会萌生想调查对方虚实的念头。陈老太要的是这种生活,张老太要的是这种解脱。
渐渐地,陈老太知道了张家的一些事。原来那个书记儿子是本县的县委书记,而大儿子是州检察院副院长。他们经常住单位,很少回家,儿媳也是工作忙,根本见不到人影儿。最后的结果是,张老太一个人在家,没人陪她说话。
陈老太也曾问过,干嘛不请保姆啊,那样你就会有人陪了。
每每这个时候,张老太总是晃着白花花的脑袋,说不好请啊。请人容易,请人心难啊。
陈老太就闭嘴不做声了。
起初那两天,陈老太总觉得怪怪的,心里痒痒,又不知毛病出在哪儿。想到自己还有三个月才出狱的儿子,心里就一阵泛酸。为什么人家的儿子就那么金贵,我儿子就这样悲惨呢?
那座漂亮的洋房子又在她眼前晃悠了,它渐渐变大,陈老太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它精致的雕花,光洁的围栏更是耀花了她的眼。她试图伸出手去,可眼前的房子忽然不见了,轻飘飘地飞到天上去了。
也许是陈老太想得多了,在和张老太聊天的时候也有一句没一句地答着。张老太倒也不在意,只要有人和她说话就是好的,她依旧重复着多日以来的话题。
我柱儿前儿说了,要让我去美国疗养,我死活也不答应。谁知道那是什么鬼地方,去了不适应怎么办?
唔!陈老太想,我儿子明天就回来了,该回去煎点儿鱼了。
我柱儿还劝我说美国怎么都比中国好,人家的疗养院很专业。
唔,唔!我儿子想吃点儿什么呢,陈老太想。
前儿州政府来了文件,我儿子可能又要升了!张老太兴奋地叫起来。
唔,唔,唔!陈老太有些不耐烦了,她得赶紧回去煎鱼,儿子明天真的要来了。
我儿媳说了,要买件羽绒衣给我。你看,这里十年也不会冷一次,哪用得着那东西!张老太有些得意,仿佛自己已经穿上了新衣,在和对面的穷婆子说话。
忽然,她听到陈老太大喊一声,住口!接着,一只未纳完的鞋底越过断墙,飞了过来。
你!!!张老太正想开口大骂,可陈老太早已转身进屋里去了。
马上,陈老太家里叮叮当当的锅碗瓢盆声响起,把张老太的叫骂声压到爪哇国去了。
陈老太的儿子终于回来了,他们带着悔恨来到陈老太面前。他们双双跪下,为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表示深深的忏悔。母子相见,泪如雨下。
饭桌上,两个儿子说起了在监狱中的学习生活,说着说着,小儿子忽然想起了个事儿。他急忙放下手里的碗,从宽大的胯兜里摸出一份揉皱了的报纸,虽然有些皱,但新崭崭的样子还在,这是一份昨天的《云南日报》。
妈,我给您念念这条新闻,这可是有关我们县的。小儿子对陈老太说着,两眼依旧不离头版的那几个粗体大字。
别,别念!那与咱不相干。陈老太一把抓住儿子的手说道,我儿回家,才是天大的新闻。陈老太兴奋地晃着两腿,拍着两只干瘦的爪子。
第二天,陈老太又倚在门前的石墩上纳鞋底了,可她一直在探望着对面的阳台。说实话,陈老太对那天的话感到很内疚,她想今天把话说明了,让张老太不要误会。
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过去了,第四天来了又走了。可张老太的阳台依旧没有开门!
怪了!上哪儿去了呢?陈老太在心内计较道。她站起身来走到断墙边上,直接把脑袋伸了进去观望。
忽然,她看见了昨天她掷进园里的那只只纳了一半的鞋底,隐在刚疯长出的野草丛里,白晃晃地伏在那里,特别刺目。
她抬起了头,望着那精致的小阳台,忽然想起来,哦!张老太也许是到美国疗养去了吧。
陈老太失望地回到家里。她忽然想起昨天儿子要给自己念的那条新闻,她想听听外面的新鲜事儿。
可是,她的两个儿子已经出去了。报纸静静地放在饭桌上,上面的字迹没有变,也不会变。
“省委常委关于审查**州检察院副院长张国林,**县县委书记张国柱的通知,下面有一篇报道:两兄弟联手收贿赂,老百姓痛斥害民虫。”
阳台的门一直关着,陈老太坐在石墩上一直地等。也许,那门是永远关着的,仿佛从来就没有开过。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