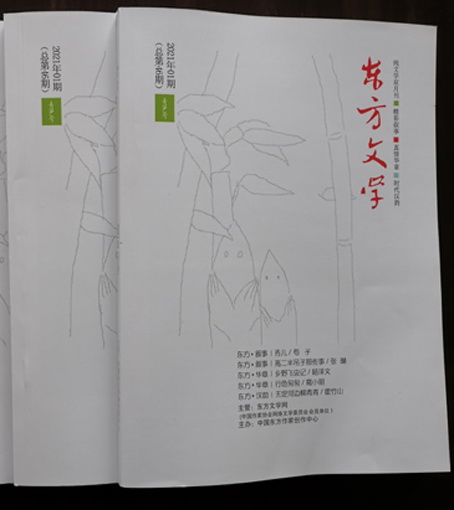诗与个体 /从查湾村的泪到济宁城的火
今夜,在孔孟之乡的济宁,诗人江雪剖开了《海子》的疼。这疼痛不止属于一位早逝的天才,更牵连着查湾村沉默的麦田,和一个家庭被诗名与苦难长久缠绕的命运。它让我们再次叩问,当生存的重量如此具体,诗歌,究竟何为。
我们深知没有救世主。自我的担当,是生命不可替代的功课。然而,正是在艺术光辉与尘世艰辛的巨大裂隙中,诗歌点亮了它的意义。它并非尘世的拯救者,而是精神的火种。这火种无法替代生活,却能在长夜里提供温度、见证不屈,让孤独的个体听见回声,让寂静的夜晚孕育雷鸣。
今夜,江雪先生以言传光,将那疼如种子般解析、埋入倾听者的心田;朱继德先生则以诗续火,铸字为碑,让瞬间的感触汇入永恒的江河。他们并非建造纪念碑,而是成为火种的守护人,以诗为舟,渡人亦渡己。
我被这样的夜晚点燃。下面这首诗,便是对这场从疼痛出发、抵达共鸣与照亮的精神仪式的记录。谨以此写给两位掌灯者,也写给所有在汉语的骨缝里等待一场雪崩的灵魂。
真正的诗,永远从裂缝中扎根,在挚爱中绽放。而真正的歌者,是在无人处执炬,将寂静唱成雷鸣。
诗火渡夜
今夜,济宁的冬被一句句诗烫醒。
亚龙书城的灯像低垂的星群,
照见百人如麦垄 静默,饱满,等待风与雪。
在此,听江雪(卜一)剖开《海子》的疼;
归去,读朱继德先生新落的《疼痛里的火种》。
两重声音,一道光痕。
诗歌从未远离,它蜷在汉语的骨缝,
在孔孟的大地上,等一粒火,等一场雪崩。
朱继德先生以诗为舟,与江雪夜渡,载满城星火。
他将疼痛、麦地与太阳熔铸一炉,
铺成一条李白走过、而我们仍匍匐的诗途。
他是灵魂的造影师,只顷刻,
便让海子的炽烈、江雪的清辉、
古城所有未言说的心跳,跃然纸上。
这般快手神笔,若非在文渊中泅渡,
在诗思里深耕,怎能如此锋利地
截取太白湖的魂魄,又如此准确地
切入古运河激流漕船过闸的脉口。
而江雪先生,以三百万文字为柴,六部专著为窖,
从《星星》到《诗刊》,从东方到远方,
他始终是那酿酒的人。
将岁月、苦难与炽爱封坛,
待启封时,倾出醉彻肺腑的凛冽醇香。
今夜他俯身书城的灯下,
将海子那份疼轻轻剥开,
如解一颗倔强的种子,埋进运河岸的冻土。
这不止是一场讲座,这是一次引燃。
他让诗歌从缥缈的神话,
落成可触的血脉、可共鸣的颤抖,
也让今夜每一双倾听的耳,
成为诗意大地的耕者与野火。
两位先生,一者以诗续火,一者以言传光;
一者铸文字为碑,一者化疼痛为桥。
他们共同印证。
真正的诗,永远从疼痛的裂缝扎根,
却在炽爱中绽出闪电;
而那些被铭记的歌者,永远在长夜执炬,
在无人处 把寂静唱成雷鸣。
今夜,济宁的雪或许未覆屋檐,
却已落进百人胸腔,
落于运河迂曲的岸,
孕育一座城、一个慌乱的春、
万亩待燃的麦浪。
致敬所有在寒夜里守护火种的人。
诗心不灭,灵魂常青。
也愿今夜所有与江雪照面的人。
长歌当哭时,不忘将一滴泪,
洒向查湾村外的孤丘、端午时节的汨罗江;
高歌猛进处,总能把一声声呐喊,
寄给星辰大海、诗与永不投降的远方。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