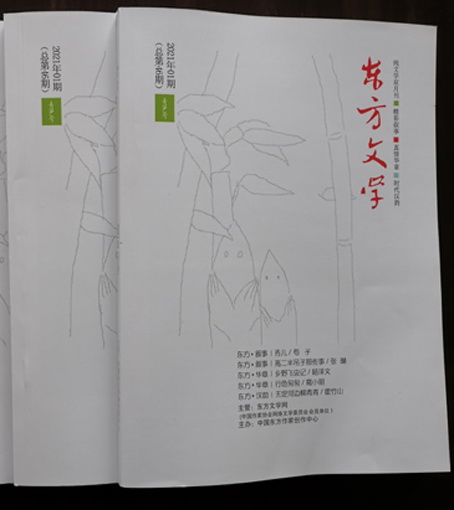诗人顾城曾坦言“你可以采来玫瑰的香气,只有跟春天在一起,你的手上才有花朵”。读罢青年诗人王树立的诗集《蜕皮的蛇》,我有这种跟春天在一起的感觉,“心上、手上永远有花朵”的芬芳。
“我将心灵的碎片献给你/那是我亲手播撒的花朵/由此我就展开一条河流/在清丽而安静的春天的夜晚/让流水把我的花瓣带走/而那些碎片的飘飘移动/在水面上她们紧紧裹着/我旷世美丽的伤痛”(《潮漫心语》)。我们说,真正的诗人都是“自然”的儿子,在社会愈是向物化、俗化发展的今天,读者愈是需要听到诗人那来自内心的本真、自然和带有个性特色的声音。这种心灵与外界撞击而爆发的由衷情愫 ,是生命的自然驱动,是生命热源的鲜活体现。“我将心灵的碎片献给你”,是诗人隐喻世界的真实呈现,是诗人“将生命化作一首绝美的诗呈现给你”的纯洁表白。因为“心灵的碎片”是“我亲手播撒的花朵”,是“我旷世美丽的伤痛”。屠格涅夫对这样的抒情与象征的自然融合,曾称之为“自己的声音”。这种实实在在的言说,用之于王树立的诗,绝无夸赞之嫌。他的诗一如他的诗集的名字《蜕皮的蛇》,那陈腐的“皮”蜕去后,是现代的风姿和新生活的品韵,是他潜意识中所向往的个性抒发。比如:“有时/我觉得自己像轻浮的白云/一个人游荡/却是向前/假如有一天/你在窗前把我瞭望/别怪我轻轻掠过/没有声响/像你这样/在窗前独自幻想/永远都是/渴望”(《浮云》)。诗人“像轻浮的白云”,“却是向前”,有一种勇力于心,而“你这样/在窗前独自幻想”,不能前去一步,“永远都是/渴望”。诗中的画家笔意暗喻着“妙神妙理”(脂砚斋语),赋予“浮云”的特殊含义。同时对“向前”者,“幻想”者或歌颂之或警惕之,皆有明示。诗中的隐喻是高超的,其间挟着心语的魔力。
《一扇门》也可谓以形传神之作,诗中用自然微妙的话语隐喻了一种人生和多种世态。
一扇门
虚掩了很久很久
没有人推开
也没有人走出
静静地虚掩着久久
在为谁守候
在为谁等待
你这扇虚掩的门哟
总在别人的手中
转来转去
从未自己转动过一次
一旦无人问津便寸步难行
生活中,“总在别人手中/转来转去”的人很多,有如影子总是追随着主子。这仅仅是一种表象,诗人透过这层面上的常理,对“一扇门”进行了挖机。他用心与心交流的形式,向“一扇门”进行坦诚的对话:“在为谁守候/在为谁等待” 。是“一扇门”就该尽其所能,何必把自己的价值丢失,而靠他人去抬高呢?当然“一扇门”也有自己的苦衷,它也许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制约,其身是不自由的。再说,这门又为何被世人遗忘了呢?诗中的隐喻义还远远不只这些,有不同感触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个切入点,找到一种理趣。由此可见,王树立的隐喻世界是博大的。诗中哲理的揭示有它的历史厚度,哲学高度。这种诗的诗情和哲理的结合,具有张力和美感的弹性,能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欣赏空间。有点不尽人意的是,这首诗的结尾,把“没有人推开/更没有人走出”的“一扇门”的隐喻世界缩小了,仅仅给人的是不能自己主宰自己的“狭小天地”。世界是复杂的,诗人的触觉点是多角度的,不然的话,就会留下一些不应有的遗憾。“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刘载熙《艺概》)。王树立深知其妙,留下不少绘形绘色的精妙诗句,如:“我只想是鱼/能和你做一生长长的漂流”(《心河》);“我是陆地的游子/在海洋里/崛/起”(《孤岛》);“同夕阳一道/生成了一把永远燃烧着的野火”(《野火》);“将粗壮的枝干扭成了一种/飞翔的姿态/凝固成一种伟大的意志/一种精神”(《十匹马,五只鹰》);“托一片蓝天/遮一世清凉/——给你,我心中美丽的姑娘”(《树的诺言》)……
是的,人的高贵正在于用心灵补五官所感,括天地而贯东西,揽实景而追虚像。我想王树立定会心领神会,去深情呼唤美好人生,寻求一种精神文化品格的感合,继续隐喻世界的真情表露,“然后脱胎换骨/变成一只鸟/高高举起这不死的头颅/向着海洋长啸”(《蝙蝠冷吟》)。
一个拥有隐喻世界的独特美妙的王树立“是雷/骤然在冬季里响起/”(《诗神的足迹》)。
1999、12、6日 鄂州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