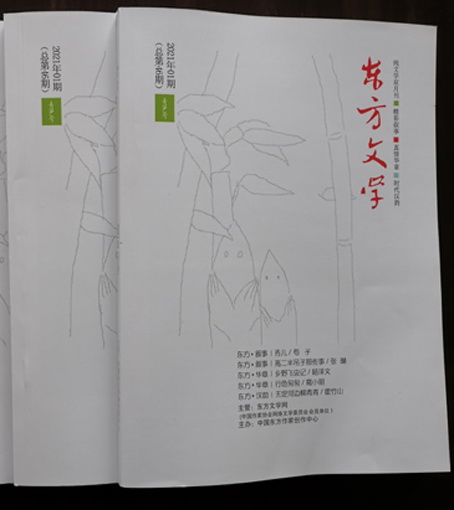西渡:灵魂的构造——骆一禾、海子诗歌时间主题与死
摘要:骆一禾和海子被视为一对志同道合和有着相近的风格特征的诗人,其诗歌主题也多有重合。时间主题和死亡主题在骆一禾和海子的诗歌书写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但在这些主题的具体意含上,两位诗人之间存在深刻的差异、分歧以至对立。在时间主题上,骆一禾信仰新生,讴歌明天;海子则膜拜过去,具有鲜明的原始主义倾向。在死亡主题上,骆一禾以生命蔑视死亡,并通过牺牲将死亡转化为新生;海子则把死亡视为生命的归宿而倾心于死亡。体现在时间主题和死亡主题上的这种深刻差异反映了两位诗人精神构造乃至精神原型的不同。
关键词:骆一禾;海子;时间主题;死亡主题;精神构造;原型
骆一禾、海子在诗歌主题上存在多重的交叉叠合,两人早期都以青春主题、女性和爱情主题为抒写中心,由此过渡到对农耕文明的歌颂,最后同时变而为成熟时期以行动主题为抒写中心的阶段。其他如关于飞行的主题,力量和速度的主题,也都为两人诗中所共享。但两人诗歌主题上的这种交集和呼应,丝毫不能掩盖其诗歌主题在具体意含上的深刻分歧和对立,某种程度上,正是上述交集使这种分歧和对立的性质变得更为醒目。骆一禾的新生主题与海子的原始主义信仰的对立,骆一禾对于生命的信仰与海子的死亡情结的对立,骆一禾对不止拥有一个灵魂的信念与海子孤独主题的乖忤,骆一禾的光明颂与海子夜颂的大异其趣,一定会给细心的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骆一禾的历史反思和社会批判主题则是海子几乎不曾涉及的。骆一禾的诗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社会内涵,其终极诗歌理想是在一个共同体价值崩塌的时代,以诗歌作为粘合剂重新建基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并以自己的青春之血为之注入新的热情与活力,从而恢复业已丧失的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从这些普遍的抵牾,不难看出两人心理结构、精神构造方面的巨大差异。用荣格心理学的术语说,他们的“精神原型”不同;用骆一禾的诗歌批评术语说,他们各有其极为不同的“诗歌心象”。实际上,即使在那些看起来相通的主题中,骆一禾和海子往往也表现出相当不同的精神意趣和价值诉求。譬如,情爱主题在两位诗人的创作中都占有很大分量,但是骆一禾的个人情爱主题最终上升为对普遍的、绝对的“无因之爱”的颂赞和坚信,海子则始终未能摆脱个人情爱失意带来的心灵创伤,以至走向了对爱的否定。骆一禾的诗歌主题,可以用孔子的话一言以蔽之:群。而海子的诗歌抒写归根结底是一种自我表现,是其心理创伤体验在不同诗歌题材和体裁中的不断变奏和复现。海子的诗歌主题,也可以用孔子的话一言以蔽之:怨。诗歌主题上的这种种分别,反映了两位诗人精神构造的深刻差异。下面我们试从时间主题和死亡主题在两位诗人具体诗篇中的展开,探索构成其各不相同的精神构造的秘奥。
一、新生与怀古:背道而驰的时间主题
骆一禾和海子都对农耕文明有深厚的感情,两人都写过很多歌咏农耕文明的诗篇。在一些人看来,这也是他们的孪生性的重要证据。但实际上,海子和骆一禾对所谓农耕文明的感情并不一致。海子对农耕文明确乎一往情深,而骆一禾虽然对农耕文明诗意的一面与海子有近似的感受,但却对农耕文明的封闭性及由此带来的保守性有着理性反思,由此导致两人绝然不同的时间观。骆一禾的写作是向着未来,为了未来的,而海子的写作则是怀古的,膜拜往昔,膜拜原始。这种不同的时间观在表面的“互文”下呈现了迥然不同的诗歌风景。
在骆一禾看来,华夏文明的大树已死,它过去的光荣,就像其图腾——龙—一样,“是一个漫长的没有意思的故事”。它留给我们的遗产,只是一些断残的遗址。为此,他告诫我们:“不要做历史的继承人/除去它的智慧/还要承其疯狂/做古代历史的继承人是很危险的。”(《腾空之美》)置身旧文明零落荒凉的遗址,诗人一心所系唯在新生。他说,五四时期“中国文明在寻找新的合金,意图焕发新的精神活火,而这一努力,迄今尚未完成”。因此,“中国的有志者,仍于80年代的今日,寻找自己的根,寻找新思想以冲刷陈腐的朽根,显露大树的精髓,构成新生”[1]。新生因此成了骆一禾最重要的诗歌主题之一。它第一次出现在1983年9月至1984年1月期间所写的《河的传说》中。自此之后,这一主题就不断回响在骆一禾的诗中,贯穿了其诗歌创作的始终。长诗《大海》第十一歌《新生》是一曲关于新生的交响诗。在骆一禾看来,新生乃是生命的“抗命而作”,它腾起在遗址的断垣和死亡的棺椁上,是“围绕死亡”而“灵息吹动”,是以“龙马精神”战胜死亡。因此,它既是安魂曲,又是欢乐颂。“新生”有两个伟大誓言,一个是“与一切而至万灵”,另一个是“叫一个人坠落就是叫一个人坠落”。① 第一个誓言的意思是,新生具有超个体乃至超人类的性质。换句话说,新生就是生命本身的定义。所以,骆一禾说:“凡有生命冲动云蒸霞蔚/必有新生。”因此,人的存在作为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和“一切而至万灵”乃是浑然的一体,一切有我,我也有一切:“千载的美景千载难逢/里面必有我的初衷。”那么,“抛弃一切形相,拥有一切形相”也就是新生的精神。新生因而无畏于死,并蹈死而行:“请雷霆把我殛灭,放下心/请阴电和阳电相反相成,请一一怀孕/请新生。”(《大海》第十六歌)第二个誓言引用了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仗着父亲代达罗斯所作蜡翅飞近太阳、翅膀熔化而坠亡的典故。飞行,在骆一禾的眼中,乃是最能体现新生精神的行动。然而,对于天生不能飞行的人类,它也是最危险的行动:“我时时看见枭雄的儿子们/在腾达中独自焚毁。”这一誓言的意思是,新生是成败难料、前途凶险的冒险行为,充满了不可预测的恐怖和命定的牺牲,它的道路也因此“不是一往无前”,而是曲折艰危的。新生因此是不为自己预留出路的行动:“当我建筑的时候/我根本无意逃遁:朝着死亡的拜物/蓖麻刻在石上/人在自己心中,我/要出路干什么”(《大海》第十二歌)。生命最大的罪恶不是死亡,而是无力从必然的死亡中新生,它所愧对的也唯有新生,为此诗人要“从泥沙里仰望新生/举起双手,向天空谢罪”。实际上,对行动的人来说,除了死,没有什么平安之路:“在前往他乡的路上/不论是凶是吉/这条死路总该平安。”(《人歌》)既如此,死亡也就无可畏惧了。我们将记起,当骆一禾为海子的猝然离去而祝祷时,所用的也正是上述诗句。[2]然而,正因如此决绝,新生才是“可赞美的行动”。可以说,骆一禾对新生的倾心既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智慧。
骆一禾的写作因此是向着未来,为了未来的。然而海子却不是这样。海子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原始膜拜。对他来说,越是古老的,就越是吸引他:“这只原始的杯子使我喜悦/原始的血使我喜悦部落愚昧的血使我喜悦。”(《太阳·土地篇》)② 所以,海子总是倾心于最早和第一:“我们的嘴唇第一次拥有/蓝色的水/盛满陶罐/还有十几只南方的星辰/火种/最初忧伤的别离//岁月呵//你是穿黑色衣服的人/在野地里发现第一枝植物/脚插进土地/再也拔不出”(《历史》),“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海上婚礼》)。海子说“我和过去/隔着黑色的土地/我和未来/隔着无声的空气”(《我,以及其他的证人》)。这么说,海子似乎和过去、未来都是隔绝的,但实际上,土地是导电的,空气却是绝缘的,所以海子对过去倾心有加,却将自己与未来隔绝开来。海子的眼光总是向着过去,有时恨不得退回母腹:“母亲如门,对我轻轻开着”(《思念前生》);有时甚至想退回到野兽的身体:“庄子想混入/凝望月亮的野兽/骨头一寸一寸/在肚脐上下/像树枝一样长着”(《思念前生》)。写于1983年的《农耕民族》也是这种向着过去的眼光的产物:“在发蓝的河水里/洗洗双手/洗洗参加过古代战争的双手/围猎已是很遥远的事/不再适合/我的血/把我的宝剑/盔甲/以至王冠/都埋进四周高高的山上/北方马车/在黄土的情意中住了下来//而以后世代相传的土地/正睡在种子袋里。”海子《神秘故事六篇》中的《南方》一篇,讲述了一个81岁的老人在一幅神秘的返乡地图指引下反时间旅行的故事,最后主人公回到了故乡,“母亲坐在门前纺线,仿佛做着一个古老的手势。我走向她,身躯越来越小。我长到三岁,抬头望门。马儿早已不见”。这个故事正是海子的“原始膜拜”心理的象征演绎。对于这一神往于过去的心理惯性和特殊精神结构,在《太阳·断头篇》中,海子另有一番夫子自道:“于是我先写抒情小诗再写叙事长诗,通过它们/认识许多少女,接着认识她们的母亲、姑母和姨母,一直到最初的那位原始母亲/和她的男人。”
海子《太阳·七部书》之一的《诗剧》也可以说是一曲反向进化之歌。长诗劈头一句,“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然后,海子顺着一条反向进化之路走向了猿:“他离弃了众神离弃了亲人/弃尽躯体了结恩情/血还给母亲肉还给父亲/一魂不死以一只猿/来到赤道。”接着,又从猿走向了乌鸦,最终走向了万物之母。这是一条逆时间而行的道路:“石头滚回原始而荒芜的山上/原始而荒芜的山退回海底”,“船只长成大树/儿子生下父亲”。在这条反进化的道路上,诗人经历了他的由人而猿而乌鸦的变形记,其终点是一把剑,一把屠戮和血腥的剑,并在剑的狂热颂歌中结束全诗:
剑说:我要成为一个诗人
我要独自成为一个诗人
我要千万次起舞千万次看见鲜血流淌
剑说:我要翻越千万颗头颅成为一个诗人
是从形式缓慢而突然激烈地走向肉体
从圣人走向强盗。从本质走向粗糙而幻灭无常的物质。走向一切生存的外表。
在海子的最后一部长诗《太阳·弥赛亚》中,海子沿着这条路走得更远:他从人类的尽头走到了物质的尽头,走到了最坚硬的物质——石头,又从石头推进,应该说后退到了世界的开始——虚无。在这个原始的虚无中,世界获得了它唯一的形式——吃:
石头不是
世界的开始
是虚无。虚无中
原始只有
一种形式
它就是吃
到这个时候,海子完全成了一个虚无的歌唱者,一个高歌着“没有”、向着虚无迈进的诗人,一个焚毁意义和价值的纵火的囚徒:“我不能歌唱我没有棕榈/没有铁锅没有草原没有三块岩石/没有大理石没有葡萄园/我不能哭泣没有鸽子没有山楂/我只有你,白色的火红的你//我没有死亡我没有生命我空无一人/我没有伴侣没有仇恨也没有交谈/……//我没有形体没有真理没有定律/我没有伤疤没有财富/我没有盘缠没有路程/没有车轮滚滚没有大刀长矛/我没有回忆也没有仇恨/我甚至没有心情。”(《太阳·弑父》第十三场中的“纵火犯”之歌)
海子的原始膜拜最终把原初和原始变成了价值的来源。对于海子,原始不仅意味着生命的丰盈和充沛,还意味着创造和力量。所以,海子一直都在滔滔歌颂“原始”:“这原始的杯子使我喜悦/原始的血使我喜悦部落愚昧的血使我喜悦/我的原始的杯子在人间生殖一滴紫色的血/混同于他从上帝光辉的座位抱着羔羊而下。”(《太阳·土地篇》第三章)“原始性”成了海子梦寐以求的目标。某种程度上,诗、酒、气功,都是他借以抵达这一“原始性”的渡船,他试图借助这些外力的帮助体验生命之醉。他曾如此描绘这一状态:“这是一种突然的、处于高度亢奋之中的状态,是一种使人目瞪口呆的自发性。诗的超现实平面上的暗示力和穿透力能够传递表达这种状态。这时,生命力的原初面孔显现了。它是无节制的、扭曲的(不如说是正常的),像黑夜里月亮、水、情欲和丧歌的沉痛的声音。这个时候,诗就是在不停地走动着和歌唱的语言。生命的火舌和舞蹈俯身于每一个躯体之上。火,呼的一下烧了起来。”[3]
循着这一思路,诗人与原始力量的关系在海子那里就成了评价诗人和诗歌的依据。他认为,天才的诗人(海子把他们区分为“深渊圣徒”和“早夭的浪漫主义王子”两类)“都活在这种原始力量的中心,或靠近中心的地方,他们的诗歌即是和这个原始力量的战斗、和解、不间断的对话与同一”,而“我们大多数的人类民众们都活在原始力量的表层和周围”,而在最伟大的诗人——亚当型巨匠(米开朗琪罗、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那里,“原始力量成为主体力量,他们与原始力量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造型的和史诗的,他们可以利用由自身潜伏的巨大的原发性的原始力量(悲剧性的生涯和生存、天才和魔鬼、地狱深渊、疯狂的创造与毁灭、欲望与死亡、血、性与宿命,整个代表性民族的潜伏性)来为主体(雕塑和建筑)服务”。[4]893
从这一“原始性”立场出发,海子对古典理性主义做出了严厉的批评。海子认为古典理性主义貌似生命的觉醒,实为对生命的斫伐,貌似让我们睁开了眼睛,实际上却使我们陷入失明状态:“古典理性主义携带一把盲目的斧子,在失明状态下斫砍生命之树。天堂和地狱会越来越远。我们被排斥在天堂和地狱之外。我们作为形式的文明是建立在这些砍伐生命者的语言之上的——从老子、孔子和苏格拉底开始。从那时开始,原始的海退去大地裸露——我们从生命之海的底部一跃,占据大地:这生命深渊之上脆弱的外壳和桥;我们睁开眼睛——其实是险入(当为“陷入”之误——引注)失明状态。原生的生命涌动蜕化为文明形式和文明类型。我们开始抱住外壳。拼命地镌刻诗歌——而内心明亮外壳盲目的荷马只好抱琴远去。”[4]890
从心理根源上说,海子逆向的时间观源于他对童年经验的留恋。从出生到15岁赴北京求学,海子在乡村生活了15年。显然,这一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精神气质和心理构造。淳朴的乡村生活和四季轮回的美丽景色在海子心里留下了美好记忆。15岁以后,海子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度过了他的青春期。环境的变迁(对于海子就像一次野蛮的移栽)使他很长时间(相对于他短暂的生命,这个时间称得上漫长)难以适应,与身边同学的年龄差距,又使他在身心发展的关键时刻缺乏沟通和倾诉的对象。也许,正是这些造成了海子成长的焦虑。回顾“金色的童年”成了海子缓解这一心理焦虑的手段,假期的返乡则成了“回顾”的庄严仪式,不断固化着其拒绝成长的心理趋向。
从个体心理学上说,拒绝成长、拒绝从天真状态进入经验状态的海子,应该说还没有完全从心理上断奶——也许在他青春期二次断奶过程中发生了某种迟滞,导致母亲成为一个笼罩性的原型,成为他一生挣脱不开的“母亲势力”;也许远离故土的创伤体验,让海子如此怀恋母亲安全、温暖、包容的怀抱。对于海子,恋人也只是母亲的替身:“心上人如母亲……一样寂寞而包含。”(《但是水、水》)他在恋人身上寻找一个母亲,以至他的情诗里不断出现母亲的身影。事实上,在海子的爱情房屋里,一直生活着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恋人反倒退隐不见了:“爱情房屋温情地坐着/遮蔽母亲也遮蔽儿子。”所以,海子一直唱着“一支回归母亲的歌”(《太阳·土地篇》),并渴望重新接续我们出生时被强行剪断的脐带:“让我们从近处,从最近处而来迫近母亲脐带。”(同上)海子对于黑夜和死亡的向往,其实也是对母亲势力的回归。这种“恋母”心结,成为塑造海子回溯性时间观的另一重要心理动力。海子的原始主义,实际上就是这种个体经验的放大和普遍化——海子诗中民族和文明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复制了诗人的个体经验。
1987年前后,海子诗歌风格突然由宁静柔美而趋向激烈狂暴,核心意象由水和月亮一变而为火和太阳,主题上也从歌唱爱与包含转而礼赞暴力与复仇,这往往被视为海子由母性走向父性的标志。③ 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海子在诗学上区分了父本与母本两种艺术创造类型,似乎也为这一转换提供了动机上的说明。其实,诗人的上述转向不过是从一个经验的母亲转向一个更为原始的母亲,从一个爱与包含的母亲转向一个愤怒的、复仇的、毁灭与破坏的原始母亲、神秘母亲。从根本上说,这一转向与更具造型力和作为创造意志体现的“父亲势力”没有多少关系。事实上,海子虽然对“父本”艺术家的造型力、强力意志和奴隶般的体力、劳作心向往之,但在心理能力和精神气象上都不具备向“父本”转向的条件。他视为同道和血肉兄弟的浪漫主义诗歌王子,在创造类型上也属于“母本”艺术家。海子把他们看作夏娃血统的最早传人,“是夏娃涌出亚当,跃出亚当的瞬间”,传达着“夏娃最早的咿呀之声”,“她的自恋与诉说”。[4]892也就是说,海子转向的心理逻辑和美学逻辑始终是统一的,这一逻辑就是他的母亲向往和原始主义决定的回溯性时间观。
二、向死而生与视死如归:云泥悬殊的死亡主题
骆一禾和海子都是敢于直面死亡的诗人。“死”字在他们笔下出现的频率,几乎不相上下。据《骆一禾诗全编》和《海子诗全编》电子文本统计,“死”在《骆一禾诗全编》中出现504次,在《海子诗全编》中出现548次,考虑到《海子诗全编》的篇幅略大于《骆一禾诗全编》的情况,这个频率可说惊人一致。然而,同样直面死亡,两人所呈现的诗歌风貌却有霄壤之别。一言以蔽之,骆一禾是“向死而生”,海子是“视死如归”。骆一禾直面死亡,是为着生命的缘故。对于他,死亡虽然是生命的背景,但却无法剥夺生命的意义,他并以爱和未来的名义拒绝死亡对生命的入侵。因此,骆一禾热爱生命,尽管他英年早逝,他留给世界的遗嘱却是:“我们要好好活下去。”④ 海子却把死亡视为故乡,对于他,死就是回家,就是还乡。因此,海子一心向往死亡,最终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骆一禾始终是一个生命的热情讴歌者。骆一禾热爱生命,而且始终坚持生命要互相热爱。早在他写作的起步阶段,他就写下了这样深情的诗句:“生命不能/热爱生命? /谁忘得了谁的光明……”(《无名的深情》)。他对生命的这般深情贯穿于其诗歌创作的始终:“如果生命是腾跃四射的火花/你又怎能牵挂物质的灰烬”(《海滩(三)》),“你们在我的手艺之中/不只是灵魂而是我的生命”《手艺与明天》),“我时时念起生命短促的名字/它的节奏像锋刃一样使人狂喜”(《风景》),“而生命此刻像矿石一样割开矿脉/爱的纯金把我彻底地夺去”(《身体:生存之祭》),“生命:不论它是在沉默/还是在笑着,虽然没有希望/也不论在什么地方/它不总在我的胸怀么”(《世界的血·雪景:写给世代相失的农民和他们的女儿》)。骆一禾认为,生命是大于个人的存在。因此,热爱生命并不是以生命为计算,以博取利益和荣名,或者把生命如财宝一样秘藏起来。这类行为不但不是热爱生命的正当方式,而恰恰是生命的败坏和堕落。骆一禾鄙弃苟活和偷生的行为,那种匍匐和爬行、明枪和暗箭、权谋和霸术,“换算金币,烂醉青楼/忍受猖狂,在自大狂的狺吠里默默偷生”(《大海》第十五歌)。他说:“以生命作为技巧,你感到耻辱。”(《非人》)生命说到底是用来创造和行动的:“升翔于曙光之际的苍鹰/鸷猛地击开彩绘的中心/那有力、有为和有生”(《世界的血·雪景:写给世代相失的农民和他们的女儿》),“力是生命唯一的定义”(《河的传说》)。“有力、有为和有生”,这是生命对人的召唤,也是热爱生命唯一正当的方式。与以生命为投资或赌注相反,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奉献,这是生命自己的歌:“请奉献纯洁气质、人之精英/追蹑命运/第一次牺献铭记永世。”(《大海》第二歌)因此,对于骆一禾,生命的梦想“永远是新生”,而不是做祖先遗址和废墟的守陵人。
故我以一生作为离去完成我的性格,
并求得青春长在
(骆一禾《世界的血·世界的血》)
“以一生作为离去”的意思就是向死而生,就是把一生作为对死的准备。这样的生存态度意味着:随时可死,因为随时有赴死的勇气;永远向生,因为永远有生活的决心。这也是对死亡的最大蔑视。基于这一以“离去”为展开的生存的精神和意志,骆一禾在《世界的血·生存之地》中对死亡发出了最深沉、最有力的诅咒:
——我绝对以黑暗蔑视死亡。
——以死亡作为技巧,只是另一种庸人。
——不能永远生活,就迅速生活。
——我的梦幻滋长,生活也随之滋长。
——我看见死亡始终暧昧。
在更早的诗中,他说:“我不愿我的河流上/飘满墓碑/我的心是朴素的/我的心不占用土地。”(《生为弱者》)在这动情的表白里,我们听到了年轻的诗人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死亡似乎柔弱然而绝然坚定的拒绝。上面已经引用的《生命》一诗表明了诗人对死亡的基本态度:“我不爱死不畏死也不言说死/我不歌颂死/只因为我是青春。”站在生命的立场上,诗人对死亡不爱、不言说,更不歌颂。他永远站在它的对面。他说,“我并不信任死亡”(《世界的血·生存之地》),他怀疑“是否真有什么死去”(《修远》)。诗人相信的乃是“注定易死的不以灭亡为归宿”(《世界的血·俄底修斯和珀涅罗珀》)。但是,诗人也无畏于死,并敢于与死亡对质:“我宁可见到你们的全部深度,与死亡对质/哲学在生存里死去/而诗章也是开始生存。”(《身体:生存之祭》)
对于骆一禾,诗就是生命的同义语,生命将永远以自身腾射的钢化火焰凌越于死亡,并使死亡相形见绌。这是他始终不渝的信念:“这是生命灌入会死之躯的喷射/也是生命之躯对死亡作出的召唤/这召唤比死亡更热烈。”(《舞族)因此,生命就是与必死的命运搏战:“也许行动失败/而得救总是偶然的/我们一生都在搏斗”(《双重艺术家》),“这抗志而非的搏战如日中天”(《世界的血·太阳日记》),“而死者以空旷袭击我们/在我为他们所凿下的鱼龙里/骑虎相搏”(《世界的血·屋宇》)。
诗人说:“不惧死亡者/必为生命所战胜”(《屋宇》)。这是因为不惧死亡而进入死亡者,已将自己交付给生命的洪流,从而化身为这洪流中的浪花。只要无限的生命长在,这一朵浪花便永远不会干涸。这是个体生命进入生命全体而实现的转化,转化的中介则是牺牲。在诗人看来,勇于生活者,也必勇于死亡。通过牺牲,死亡成为个体生命通向生命大全的开口和道路。骆一禾早年的诗中说:“世界说需要燃烧/他燃烧着/像导火的绒绳。”(《先锋》)牺牲把死亡变成了“导火”的绒绳,通过个体生命的献出,生命的大全得以现身。在后来的诗中,他说:“第一次牺献铭记永世/此去务必心地坚贞/与万灵相遇,万物奔腾/惟有无辜。”(《大海》第二歌)——正是牺牲使我们与万灵万物相遇相汇,世界因而以奔腾的生命全体向我们显现。相反,那种“阴暗里计算的力量”则只导致生命的腐败,使生命等同于死亡:“我们活着不过在殉葬/他们死了却是去牺牲。”(《舞族》)事实上,牺牲是死亡从其封闭性(死亡的无法替代的本质)中挣脱,向着生命转化的唯一方式。以牺牲的名义,生命最终将战胜死亡:“背着一袋头颅、双手和心口/与骏马长饮太阳/愿被生命战胜!”(《大海》第十四歌)“闪光的岩核种在手心/那是被生命战胜的死”(《大海》第十五歌)。
海子的死亡主题却完全在另外的场景中展开。海子当然也热爱生命。事实上,海子对于生命的热爱不亚于任何诗人。在《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一文中,海子说:“要感谢生命,即使这生命是痛苦的,是盲目的。要热爱生命,要感谢生命。这生命既是无常的,也是神圣的。要虔诚。”[5]915在1987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海子写道:“我确实是一往直前地拥抱生活,充分地生活。我挚烈地活着,亲吻,毁灭和重造,犹如一团大火,我就在大火中心。那只火焰的大鸟:‘燃烧’——这个诗歌的词,正像我的名字,正像我自己向着我自己疯狂的微笑。”[6]883站立在这些文字中心的,难道不是一个热爱生活和生命的诗人吗?海子也像骆一禾一样,呼吁诗人超越自我,进入生命。他说:“要热爱生命不要热爱自我,要热爱风景而不要仅仅热爱自己的眼睛。”[6]916他称赞荷尔德林,“热爱风景的抒情诗人走进了宇宙的神殿。风景进入了大自然。自我进入了生命。没有谁能像荷尔德林那样把风景和元素完美地结合成大自然,并将自然和生命融入诗歌——转瞬即逝的歌声和一场大火,从此永生。”[5]918但是,海子所谓进入生命和骆一禾的进入生命并不是一个意思,也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在骆一禾那里,进入生命意味着进入激越腾射、奔流不息、滚滚向前的生命洪流,在一种伟大的奉献中肯定自己。海子的进入生命是尼采式的,是要进入所谓的生命本体,在一种本能的解放与放纵中求得与世界本体的合一,他所经由的是一条自我否定之路。前已述及,这一自我否定暗中勾连着弗洛伊德的死本能。骆一禾说:“我们与光明只有生命的联系。”[《巨人》(1988)]然而,海子从“生命”燃烧中体验到的却是盲目和黑暗:“我的燃烧似乎是盲目的,燃烧仿佛中心青春的祭典。燃烧指向一切,拥抱一切,又放弃一切,劫夺一切。生活也越来越像劫夺和战斗,像‘烈’。随着生命之火、青春之火越烧越旺,内在的生命越来越旺盛,也越来越盲目。因此燃烧也就是黑暗——甚至是黑暗的中心、地狱的中心。”[6]这里同样飘荡着死亡的魅影。海子自称为“青春、爱与死”的诗人,但他的青春主题唱的并不是对生命的赞歌,虽然在《太阳·弥赛亚》中,他说过“青春就是真理/青春就是刀锋”。事实上,海子的青春主题中也常有死亡的身影飘过,而使青春与死亡、与黑暗结邻:“只有关于青春的说法/一触即断”(《海上》),“阴暗的女王就是我永远青春的宝剑”(《在家乡》),“用我们横陈于地的骸骨/在沙滩上写下:青春”(《秋》),“我的愚蠢而残酷的青春/是同胞兄弟和九个魔鬼/他一直走到黑暗和空虚的深处”(《月全食》),“我梦见自己的青春/躺在河岸/一片野花抬走了头颅”(《太阳·土地篇》)。
在海子身上,死亡和生命变成了神秘的同义语,它们总是成对地一起出现,像一对难舍难分的恋人:“大黑光啊,粗壮的少女/为何不露出笑容/代表死亡也代表新生”(《传说》),“我的木床上有一对幸福天鹅/一只匆匆下蛋,一只匆匆死亡”(《给安徒生》),“受孕也不是我一人的果实/实在需要死亡的配合”(《吊半坡并给擅入都市的农民),“车子叫生命也叫死亡。车夫叫思想也叫灭亡”(《太阳·弑》第十七场),“我要加速生命与死亡的步伐。我挥霍生命也挥霍死亡”[6]883。这种特殊的情形,似乎是受尼采美学的感染,但其实也深植于海子的天性基础和心理构造中。海子的成名作《亚洲铜》就是开始于不祥的死亡叙述:“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死始终是海子想象力围绕的一个中心。
他甚至说死亡是唯一的事实:
除了死亡
还能收获什么
除了死得惨烈
还能怎样辉煌
“在这个平静漆黑的世界上
难道还会发生什么事”
死亡是事实
唯一的事实
是我们天然的景色
是大地天空
[海子《太阳·断头篇》(1986)]
海子写于1986年《抱着白虎走过海洋》,把生命与死亡的对称美化为一对神秘的姐妹:
倾向于太阳的母亲
抱着白虎走过海洋
左边的侍女是生命
右边的侍女是死亡
倾向于死亡的母亲
抱着白虎走过海洋
这种对称甚至也出现在海子人生的顶峰时刻——当他为初恋的幸福唱出最甜蜜的恋歌的时候:
天亮我梦见你的生日
好像羊羔滚向东方
——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黄昏我梦见我的死亡
好像羊羔滚向西方
——那太阳落下的地方
(海子《给B的生日》)
在为初恋情人写的生日诗中“梦见我的死亡”,实在有些奇特,反映着诗人特殊的心理:他对于爱和死感到同样的亲昵。实际上,海子的很多情诗都同时表现着死的愿望,从早期的《打钟》《半截的诗》《爱情诗集》,到晚期的《太阳和野花》《日落时分的部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日记》——似乎海子的情诗也是为死神而写。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在海子的《太阳·土地篇》中,情欲老人和死亡老人是两位一体的同一个:“情欲老人,死亡老人/一条超于人类的河流/像血泊,像大神的花朵/…… /他情欲和死亡的面容/如和平的村庄。”海子《神秘故事六篇》中的《龟王》《木船》《诞生》和《公鸡》都在讲述这同一个神秘的对称观念。这一观念的核心意念是生来自于死:“死亡如门”(《但是水、水》),正是死把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所谓受孕“实在需要死亡的配合”,也是这个意思。《木船》的主人公无父无母,一条神秘的木船从河的上游把他载到村子里。除了喜欢画画,他的生活和平常人没什么不同,他在贫苦长大,娶妻生子,为养父母养老送终,为生存干过一切营生。当他老的时候,“那条木船的气味渐渐地在夜里漾起来了”,而当他终于合眼的时候,“那条木船又出现了。它逆流而上,在村边靠了岸。人们把这位船的儿子的尸首抬上船去,发现船上没有一个人。船舱内盛放着五种不同颜色的泥土。那条木船载着他向上游驶去,向他们共同的诞生地和归宿驶去。有开始就有结束。也许在它消失的地方有一棵树会静静长起”。这艘神秘的木船是生的象征:“就在那条木船在夜间悄悄航行的时辰,孩子们诞生了……仿佛在行进的永恒的河水中,是那条木船载着这些沉重的孩子们前进。”同时,它又是死的象征:“它像死后的亲人们头枕着的陶罐一样,体现了一种存放的愿望,一种前代人的冥冥之根和身脉远隔千年向后代人存放的愿望。”这些描写深切地体现了一种循环论的死亡和复活观念。人的生老病死被海子视为一个大地——泥土的循环过程,船的生死也是如此:人们砍伐木头建造了船,而在船消失的地方,“有一棵树会静静长起”。海子这种循环论思想,既受到传统道教(基于自然的观察和体验)、佛教(基于对个体生命的沉思)思想的影响,也有藏族轮回观念的印记。这一思想在海子各个时期的诗中都有表现:
埋着猎人的山冈
是猎人生前唯一的粮食
(海子《粮食》)
夜,这使我思念的心脏,这羞涩的经验的金属。巢入我的嘴唇,顺着我的喉咙肠道,通过我的血液、精汁流出体外。又通过灌木和兽群拣回一堆堆柔软的黄土。坟上的太阳,肿血之脸回来了。
(海子《太阳·断头篇·祭礼之歌》)
猎人生前以山为粮,死后成为山的养分。夜和空气通过呼吸,进入我们的身体,通过血液、精汁流出体外,然后进入灌木、兽群的身体,复归于黄土。生活似乎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循环中过下去,生活、生命的意义似乎也在于此,也止于此。生是死的起点,死也是生的起点,无爱于生,也无怨于死。海子复活的信念总的来说就建基于此。
基于这样的生死观,海子的诗绝少把死亡联系于悲伤、哀恸、恐惧的感情。与此相反,他想象中的死亡是温柔、安详、美丽的,甚至是幸福和欢乐的。他说:“死亡如门”(《但是水、水》);他说:“死亡如陶”(《但是水、水》);他说:“死亡是指一种幸福”(《太阳·弑》);他说:“我通过死亡体会到刽子手的欢乐”(《太阳·土地篇》);他说:“为了死亡我们花好月圆”(《太阳·土地篇》)。《早祷与枭》(1985)表现死亡的温柔,令我们想起女诗人陆忆敏的名作《温柔的死在本城》。海子把死想象成一只枭鸟,但这只枭鸟并不是什么可怕的猛禽,而是有依人温柔如小鸟,诗人请求它:“请你接住我,枭/用胸脯接住我/你要忍痛带走我。”诗人欢迎死的到来,他说:“我的身体是一家院子/你进入时不必声张。”死后的葬仪也是安详的:“死后/风抬着你/火速前进/十指/在风中/张开如枭住的小巢//死后/几只枭/分吃了你/小南风细细如笛地吹在下午/所有的小蜻蜓/都找不到你的坟墓。”这里,枭分食尸体的过程,同时也是死向生命回归的过程。就此而言,海子似乎和骆一禾对于死向生的敞开和转换信念达成了一致。但骆一禾的信念建立在对新新顿起的生命之未来的信念上,同时它要以牺牲为中介,海子则是在循环论的基础上达成的慰藉。
由于对死的这种亲昵,海子大概也是把死亡表现得最美的中国诗人。在《给萨福》中,诗人把“凋零的棺木”形容为“一盘美丽的棋局”;《九月》把死亡和繁盛的野花联系在一起:“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汉俳·草原上的死亡》更把死表现得圣洁而美好,如一个神圣仪式:“在白色夜晚张开身子/我的脸儿,就像我自己圣洁的姐姐。”在《我所能看见的妇女》⑤ ,海子把死亡和女性的美和爱并列,让死亡也变得轻盈、纯净、温柔、安详而静美,其特殊的死亡想象力竟让尸骨变成了妇女们的美丽嫁妆:
我所能看见的少女
水中的少女
请在麦地之中
清理好我的骨头
如一束芦花的骨头
把它装在箱子里带回
我所能看见的
洁净的妇女,河流上的妇女
请把手伸到麦地之中
当我没有希望坐在一束
麦子上回家
请整理好我那零乱的骨头
放入一个红色的小木柜,带回它
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
但是,不要告诉我
扶着木头,正在干草上晾衣的
妈妈。
对海子来说,生之美丽也是根植于死的。在《肉体(之二)》中,海子写道:“迎着墓地/肉体美丽。”自杀的过程也被海子提炼为美的意象,自杀者的内心搏战,自杀过程中的暴力、惨酷被统统滤去,只留下“死亡的唯美”:
伏在下午的水中
窗帘一掀一掀
一两根树枝伸过来
肉体,水面的宝石
是对半分裂的瓶子
瓶里的水不能分裂
伏在一具斧子上
像伏在一具琴上
还有绳索
盘在床底下
林间的太阳砍断你
像砍断南风
你把枪打开,独自走回故乡
像一只鸽子
倒在猩红的篮子上
(海子《自杀者之歌》)
这里,自溺者的水变成了飘溢着家的气息的窗帘,这就不仅在比喻的意义上,而且在情感意义上把死看成了回家。由此,尸体变成了“水面的宝石”“对半分裂的瓶子”,变成了“南风”和“鸽子”;自杀的凶器也被唯美化了,暴力的斧子变成了“琴”,“绳索”变成了“林间的太阳”,“枪”变成了故乡的召唤。“瓶里的水不能分裂”向我们表明,在生与死的循环转化中,象征生命的水始终如一;瓶里的水回到瓶外的水、结合于瓶外的水,只是生命向着一个更大的生命的回归。
从对死的如此倾心中,产生自杀的念头是不足为怪的。海子很多的诗都暗示着自杀倾向。实际上,海子是把自杀当成一次重大和决断的行动来讴歌的。在《太阳·断头篇》中,海子写道:“除了死亡/还能收获什么/除了死得惨烈/还能怎样辉煌”,“死亡是一簇迎着你生长的血红高粱,还在生长/除了主动迎接并且惨惨烈烈/没有更好的死亡方式”。这种“主动而死”,是绝对的,几乎没有原因,没有理由,和骆一禾有所为的献身和牺牲不在同一意义层面上。在《死亡之诗(之二:采摘葵花)》中,海子把自杀过程写得“兴高采烈”:
雨夜偷牛的人
于是非常高兴
自己变成了另外的彩色母牛
在我的身体中
兴高彩烈地奔跑
这首诗有一个副题——“给梵高的小叙事:自杀过程”。梵高是在创作激情衰退、癫痫病数次发作、面临彻底丧失理智之际,枪击腹部自杀,并在拖了将近两天后去世的。这首诗正是写梵高受枪伤之后走向死亡的过程。“雨夜偷牛的人”显然是死神的隐喻,生命在自杀者身上流逝的过程则被比喻为牛被偷走并成为“死的皇后”的过程。枪击造成的伤口和血,被隐蔽地称为葵花,死神成了在伤者身体上采摘葵花的人。悲惨的死亡过程经过隐喻的转化,滤去了所有令人不快的成分,变得令人向往。
梵高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就是海子的故事。数年后,海子面临和梵高同样的困境,在几年的加速生活之后,海子似乎把他想要表达的一切都表达完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精华完全献给了艺术)。在经历过多次写作的高峰体验之后,海子感到身心疲惫(正如他在《祖国或以梦为马》中写的“面对大河网无限惭愧/年华虚度我空有一身疲倦”),而且某种和梵高类似的、丧失理智的恐惧,也威胁着他。于是,他做出了和梵高相同的选择。1989年3月26日,正当春天访问北方大地的时候,这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的孩子,向着轰轰作响的钢甲列车迎面走去,张开双手拥抱了他向往已久的死神。只是我们不知道,当他如此决定去死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否曾经发出那抗拒死亡的声音:“爱情使生活死亡。真理使生活死亡/这样,我就听到了光辉的第三句:/与其死去!不如活着!”(《太阳·诗剧》)这个声音来得太晚,因为这个时候,诗人已经“走到人类的尽头”,无法回头,也没有回头路了。
三、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不难认识到虽然时间主题和死亡主题在骆一禾和海子的诗歌书写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但在这些主题的具体意含上,两位诗人之间存在深刻的差异、分歧以至对立。在时间主题上,骆一禾信仰新生,讴歌明天;海子则膜拜过去,具有鲜明的原始主义倾向。在死亡主题上,骆一禾以生命蔑视死亡,并通过牺牲将死亡转化为新生;海子则把死亡视为生命的归宿而倾心于死亡。体现在时间主题和死亡主题上的这种深刻差异,正是两位诗人精神构造和精神原型的根本差异在诗歌主题学上的展开。
注释:
① “与一切而至万灵”见骆一禾《大海》第一歌,“叫一个人坠落就是叫一个人坠落”见同诗第十一歌,引自张"编:《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本文骆一禾引诗均出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骆一禾诗全编》,下文不另加注。
② 海子:《太阳·土地篇》见西川编:《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77页。本文海子引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海子诗全编》,下文不另加注。
③ 西川在《怀念(之一)》和《死亡后记》中两次提到海子1987年前后的转向,均把它描述为由母性向父性的转向。参见《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页、第923页。
④ 参见张":《心愿之乡——纪念一禾》,《倾向》第2期(上海,1990)。张"在文中说,“有两次他经历了最好的朋友的死亡,两次他都以泪抱住我说:‘我们要好好活下去!’”
⑤ 此处所用文本为笔者大学期间的手抄稿,其底本是海子在北大中文系学生刊物《启明星》(1986年第13期)上的发表稿。文字与《海子诗全编》所收《莫扎特在〈安魂曲〉中说》有多处不同。
参考文献:
[1] 骆一禾.水上的弦子[M]//张玞.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829.
[2] 骆一禾.冲击极限[M]//张玞.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859.
[3] 海子.寻找对实体的接触(《河流》原序)[M]//西川.海子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870.
[4] 海子.诗学:一份提纲[M]//西川.海子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5] 海子.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M]//西川.海子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6] 海子.日记(1987年11月14日)[M]//西川.海子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