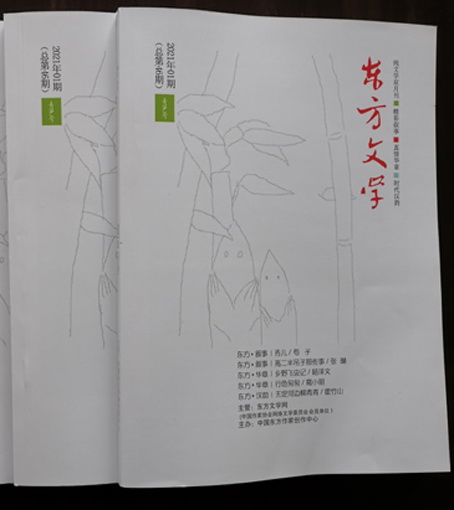眼前的世界已拥有成熟的语法
修辞感到了必要的羞耻;
当形式那最强大的美学
退让于对内容的肤浅理解
散文,已经勾引了人类。
因为年轻人像老朽一样无视隐喻
却对佩涅洛佩的绯闻保有热心,
当上百个求婚者显然都相信
同一个谣言:奥德修斯的死
已成为语言的真实——
成为世界现在的样子,成为是其所是:
那些平铺直叙的街道和商店
没有面孔的背影,也没有幻觉和回忆
而在词语之内,我们已经开始流亡
谁读出,谁就永不归来。
回地点评:
这是一首关于人的精神命运的诗,也可以读作一首关于诗的诗。借用奥德修斯的流亡故事作为脚本,针对被“祛魅”后的世界——一个平面化的、“没有面孔的背影,也没有幻觉和回忆”的、同质化的世界,作者作出了批判,他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之中人的语言状况,重新提出了质疑。
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的流亡命运,被众神赋予了神谕的奥义。但因为现代世界“众神之死”的现实,人对于神谕和命运的奥义已不能参透,而“散文,已经勾引了人类。”世界是平的;街道和商店铺陈着平庸的日常。
某种“成熟的(太成熟的,或烂熟的)语法”,阻遏着创造性语言、创造性修辞的自由发展,而“年轻人像老朽一样无视隐喻”,只剩下“对内容的肤浅理解”,因此,人的精神开始了他在“词语之内”的内在流亡;在他的世界中,隐喻失去了语言光辉的烛照。口语派甚至喊出:驱逐隐喻!而当人们以为奥德修斯及其古老神谕已经死亡,世界已经趋于平面化和庸俗化,我们内心的奥德修斯却已经开始了第二次,甚或更多次的流亡。
这首诗表达了一个尖锐的观点:作为人类精神创造的高级结晶体——诗性语言,在世界的“成熟(烂熟)的语法”中,竟然感到了“修辞的羞耻”。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